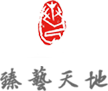
文艺评论
Comments
谭 飞
摘 要:郭启宏是中国当代剧坛公认的才子,作为唯一一位同时获得文化和旅游部颁发的戏曲、话剧双重荣誉的剧作家,他在戏曲文学、话剧创作、戏剧理论等方面都是佼佼者,素有“诗人”剧作家的美名。他以精英文学历史剧为创作方向,塑造了大量“逆行者”知识分子形象,展现了他和他笔下知识分子对人生价值和精神追求的反思和叩问。将郭启宏戏剧创作放置到精英文学与启蒙、现代性的关系中加以阐述,将郭启宏放到大戏剧的文化框架中进行探讨,在文学史思潮、戏剧史发展中明晰其戏剧创作的位置,并对其作品的精神主题、思想价值等进行客观评述和判断,是一个富有双重领域,多种指向的有益研究考量。
关键词:郭启宏;精英文学;“逆行者”
近年来,在“现代性”浪潮汹涌而至的全球化背景下,现当代文学的走向在云奔潮涌和趋向边缘的反复交叠中跌宕起伏。“现代性”与文学启蒙所主张的人性解放、人道主义有着某些异曲同工之妙,精英文学—启蒙—现代性,这三组词语之间有着意义深刻的关联[1]。
矛盾是对立统一的。“现代性”在推动经济生产进步、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也使得高雅文化日益“祛魅”为世俗文化,呈现出新的文化追求潮流。锱铢必较、精打细算的商人,精准务实、一丝不苟的工程师,斤斤计较、活在当下的小市民,这些形象正在成为当今社会一致认可的性格原型。而不计后果的叛逆与反抗、夸张绚烂的想象和激情、似乎过于虚幻的诗与远方,正在从追求实用性的当代社会里慢慢消失。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物质表象背后,人类自由的天性、远大的志向和高蹈的情怀正在变成遥远的乌托邦,便捷的单向度、碎片化文化逐渐蔓延到了整个社会。此时,精英文学如何适应无法逆转的现代性大潮,在批判和质疑中继续向前,在大众文化中坚持并彰显自己的启蒙品格,都是需要直面的问题。对此,郭启宏交出了自己的戏剧艺术答卷。
一、现代性困境中的精英文学启蒙
郭启宏出生于1940年,他见证了新中国文学思潮发展的历史进程。结合其人生阅历,在文学创作中,他无法摒弃童年时代受到的传统文学熏陶,不可避免地对十七年文学政治性“是”与“非”的价值判断进行思考,也无法回避“文革”“听将令”时期的政治运动和样板戏创作,更不会错过20世纪末各种文学思潮的突飞猛进与黯然退场,以及对新世纪、新时代林林总总各种新质思维方式的领会和思考。他的戏剧创作流露出浓郁的精英文学气息,带着鲜明的新时期启蒙特征,在对自我与世界的反思中,体现出一种视野开阔、赓续传统、跨界交融、兼容并蓄的文化使命感。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知识分子经历了暗夜里的煎熬与黎明前的焦灼,进入了一个风起潮涌的时代,他们有着要迫切唤起民族觉醒、倾诉时代心声的自发要求,体现了社会大众对人道主义关怀慰藉的共同诉求。郭启宏这一时期的戏剧作品契合了当时精英文学的启蒙主流,他创造了一批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的传统文人形象,他们坚守气节、忍辱负重、坚定前行,如司马迁(《司马迁》)、王安石(《王安石》)等。虽然京剧《司马迁》获得1980年文化和旅游部创作奖,在戏剧冲突、历史精神等方面都做到了突破,但在人物形象上仍然延续了我国传统戏剧塑造人物的共同弱点,即只在与外部环境、他者对立的层面上表达个性特征,人物流于平面化和单纯化,这距离郭启宏标志性的对知识分子人格和心理的深层探究和自我冲突还很远。
真正使郭启宏进入一个更高创作境界的,是他后来塑造的一些精神受挫、壮志难酬、垂头铩羽的文人形象。1989年之后,以戏曲创作见长的郭启宏开始从事话剧创作。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李白》《天之骄子》《知己》,作为北京人艺的传统剧目盛演不衰,被称为“中国文人三部曲”,引发出对文人及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重构问题的深层思考。李白、曹植、顾贞观、吴兆骞……他们并不完美,他们高傲而又胆怯。当他们独善其身的清高傲骨被渴望兼济天下的信念所沾染,他们的迂腐、天真、懦弱被残酷的现实之刀迎面劈来,受伤的心灵在苦难中上下求索,进而不能退而不甘,矛盾重重,留下了摇摆不定挣扎不休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张和平认为,郭启宏的作品体现出整个中国戏剧、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气韵[2]。我们研究郭启宏戏剧,探讨其笔下的主题意蕴和人物精神特质,不能脱离时代发展的背景走入封闭的乌托邦,而应该理解他讲述的故事里隐藏的知识分子精神发展史的当代阐释动机,以及他作品后面更宏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相对应的文化心理结构。从早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王安石式以一己之力推动社会变革的精英人格的憧憬和向往,到90年代以后对李白式失意文人精神坚守的同情和关爱,展示了郭启宏对精英文学启蒙的思考和坚持,以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重构的反思,呈现出一种复杂斑驳而又厚重丰赡的审美质地。这是作者对知识分子生命态度的独特观照,也暗含了作者个体思维的成长轨迹。
郭启宏笔下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转变,背后并不是空无一物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受市场经济影响,知识分子曾坚信的人文精神和启蒙原则受到了巨大的动摇。很多人发现,启蒙具有两面性,在把人们从愚昧中解救出来的同时,也容易走向以理性压迫人性的另一端,“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3]。在“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特定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仿佛失去了照亮、关怀、拯救洞穴里芸芸大众的思想精神底气。“8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从强调精英意识开始觉悟的,而到了90年代,又恰恰是从追问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虚妄性重新定位”[4],这无疑是可悲的。郭启宏的很多作品都体现了对“文革”和新时期新启蒙的反思。
洪子诚在《作家的姿态和自我意识》中分别以巴金和杨绛为例,介绍了新时期知识分子关于文学责任和精神重塑的两种态度:一类是完全介入的“英雄式”的忏悔精神,以巴金为主要代表;另一类是“我不是堂·吉诃德”式的智性思考,以杨绛为主要代表。非常巧合的是,这两类知识分子灵魂的影子都潜伏在郭启宏的戏剧作品中。郭启宏展示了从古至今中国文人骨子里一脉相承的东西,写出了发自他们灵魂深处的喟叹声,道出了千百年来他们的生命感怀,具有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
剧中李白在入世与入道之间的考量和挣扎,像极了巴金在舍弃、超脱和还债、承担之间的思考和诉说。《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云:“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哲学家牟宗三说过,道家的智慧其实就是“忘”的智慧。但是李白和巴金都没有选择忘记和超脱。他们身上打着儒家士大夫的烙印。郭启宏笔下的李白说:“鬼使神差,我总觉得后脊背上有一根无形的珊瑚鞭在抽打着我!”[5]巴金说:“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他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6]他们都说有一根自省自审的鞭子在抽打心灵。李白在听到纪许氏夸他人品好、刚眉傲骨之时,抑制不住自己的痛楚,说“李白不全是那样。他有刚眉傲骨,也有奴颜媚态”[7]。
在郭启宏笔下,李白不是孤零零存在的个体,他是中国文人的某些抽象精神代表,带着一些仿佛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像我们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纵然这英雄未必不清楚自己的迟暮、渺小和无用功,但他们答应承担的责任,推动着他们义无反顾完成自己的使命,绝不轻易舍弃。你可以嘲笑他们一本正经的迂阔和天真,但笑过之后,你也许发现,有一种心酸,正从心尖漫溢到眼眶。就像宗琰看到李白踉踉跄跄力不从心舞剑时的垂泪哽咽:“夫子,你还去么?”李白无言,拄剑而立。他是非去不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顾贞观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李白、顾贞观是古代人,又不全然是古代人,这是郭启宏运用他的想象和妙笔,寄予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悯和尊重。郭启宏本人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在李白们的身上,也有着作家本人关于人生困惑的思考和理解,他把他的书写和个人经验、人物灵魂和普世人性胶合在一起,尽管也有戏谑和难堪,但他直面知识分子的内心,自觉背负精神的重担,回望并拯救知识分子的人格。
与巴金不同,杨绛用另一种清醒,说出了“我不是堂·吉诃德”,“是什么料,充什么用”[8]。她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定位问题,这与《天之骄子》郭启宏探讨的“可以作梁的作梁,可以作柱的作柱,不能作梁不能作柱的可以当柴烧”的知识分子人生价值追寻有着相同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是偶然的,带着特定时期历史文化的血泪。杨绛以冷静淡然宽容的口吻,透露出了有着政治追求想要青史留名的中国文人心中深刻的隐痛。
这也是郭启宏笔下的李白、曹植所经历的痛苦。他们发现,政治追求和文人秉性之间隔着千山万水的距离,与救世救人相比,其实最好是先考虑救出在诸多压力下失去本性的自己。对此,郭启宏让顾贞观走出了中堂府,也走出了“心的牢狱”,这是顾贞观的顿悟,也是郭启宏的顿悟,但被囚壅丘的曹植却永远无法以坦然而平静的态度去接受现实,最后只能带着他的伤痛和困惑,“将头埋于披风之中,宛若一丘诗坟”。这也是郭启宏话剧创作的深刻之处。
二、“逆行者”的知难而进
在解构主义盛行的今天,精英文学进入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尴尬困境。郭启宏作为新时期精英戏剧的代表人物,与中国当代戏剧文学的发展和变革紧密相连,体现了精英文学对现代性困境进行反抗和突围的尝试。他的戏剧创作既没有受到商品经济物质主义趣味消费的消解,走向媚俗主义和现世主义,也没有在先锋性新感觉、新经验、现代派、后现代派的外来崇拜中迷失方向,而是以开放而自信的姿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坚持传统经典的审美根基,坚守精神和灵魂的终极关怀问题,立身于当代剧坛。
郭启宏的很多作品都体现了对人类生存荒谬处境的警醒和臆测。例如《小镇畸人》中尊严尽失的九阳小镇,《知己》中在顾贞观艰难的营救过程中吴兆骞的自我叛变……郭启宏引导读者/观众领悟剧中人物荒诞境遇里隐秘的内心感受,展现人生困苦处境下的荒诞感和分裂感。但这些人物尽管在荒谬的处境里处处碰壁,却并没有变为逃避纷扰隐居世外的陶渊明,也没有化身为醉生梦死的庄公与蝴蝶,而是成为逆行于现实的反抗者。
他作品中的人物大都带有一种逆行于潮流和现实的态势,具有理想化的反抗精神。司马迁在众人皆趋附于佞臣李和嫣的情形下挺身而出,为被污蔑的李陵仗义执言,获刑入狱;李白在永王李璘众门客皆投其所好的情形下,劝他要明白君臣之道,守大节尽大孝,引得永王心生杀念;李清照不理会旁人的看法,在改嫁和离婚上都坚持己心,而嫁与张汝舟后,夫权威慑与欺凌虐打也并不曾动摇她守护父乙彝的决心……最后这些“知难而进”的文人都摆脱不了“含冤入狱”的经历,由此引发了被囚禁或流放的境遇。
作者仿佛对冤狱和救赎的情节情有独钟,甚至成为一种症候。从司马迁、曹植、李白到吴兆骞、李清照……对含冤入狱者(或被流放者)的救赎之路是郭启宏众多作品的关键叙述线索。作品不可能离开时代境遇和作者而单独存在。一方面,冤狱和救赎展示了极端情境中人物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状态,与中国文人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息息相关,他们的自我抗争,也体现了民族精英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塑造的过程;另一方面,这种或囚禁或流放的“冤狱”梦魇,也与郭启宏本人的生命体验、人生经历不无关系。他的父亲和兄长曾先后被错划成“右派”进行劳教,最终父亲死在劳改场,兄长到死都未能脱掉“右派”帽子。幻化到作品中的,是郭启宏个体无意识“压抑”的再现,更是一种隐藏在知识分子集体文化心理和情感经验血脉里的精神创伤的浮出水面。这在与其他剧作家作品的比较中显得更加鲜明。
与同样擅长写知识分子历史剧的优秀剧作家郑怀兴相比,郭启宏对自己笔下的文人更加残忍。郑怀兴聚焦文人士大夫的价值理想、节气风骨,塑造了周伯仁、傅山、海瑞等经典艺术形象,他们在抗争强权的层面上,大多以正气浩然的“胜利者”姿态落幕,写出了一种指点江山、感慨兴亡的浪漫主义情怀,带领观众与人物一齐长歌当哭、坚守节操,慷慨动人。郭启宏笔下的文人虽然同样敢于抗争强权,但他们大多数是虽败犹荣的“失败者”,常常陷入因“冤狱”所导致的囚禁或流放的境遇中身不由己狼狈不堪,而“救赎”又往往遥不可及。作者深入发掘、放大了人物在此过程中内心苦痛,对这种不断失败的坎坷人生境遇里知识分子的人性变异和坚持的考量,于深不可测的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文化海底世界,是一种探寻和叩问。
与新时代同样拥有多套笔墨、学院派出身、以昆曲创作扬名剧坛的年轻剧作家罗周相比,郭启宏笔下的“逆行者”隐藏着作家丰富阅历背后汹涌澎湃的心灵挣扎。罗周的作品常流露出似水青春年华里惘惘的死亡主题——关于爱恋与生死,或者以人物的死亡来传达作者对历史以及生活的浓重情谊,表达人生的极致。不过在诡谲的历史和政治面前,对于郭启宏笔下处于“冤狱”和“救赎”境遇的“逆行者”而言,“死”其实反而是比“生”要容易得多的。但是,郭启宏很少以人物之“死”来解决问题。在人生的落差和人情的冷暖中,以结束生命来抵抗世俗的不公,表达内心的忿恨,这不是真正的强者所追求的尊严。郭启宏从不掩饰对生之沉重的敬畏之意。
他笔下的人物,没有绝对的“胜利者”的大快人心,也没有“以死明志”的一了百了,而是在周而复始的失败和对决中仍然勇敢地顶起形而上的重负。他为历经沧桑的剧中人吟唱出了一曲曲悲戚豪迈、响遏行云的苦魂悲歌,底子却仍然是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色调。
在创作过程中,郭启宏的精英文学历史剧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但又表现出了与之迥然不同的质地。这种区别表现在对“逆行者”背后的儒家文化精神品格的解读上。“现代性”打碎了旧的天命史观,众多新的历史观念涌动不安,作家们纷纷以虚构出来的小人物来描绘自己心目中的历史,对传统的历史英雄则往往采取故意矮化或刻意回避的方式,响应对历史的多元解构,更主要体现在对正统儒学的崇高进行消解,因为正统儒学与传统历史的王权崇高往往密不可分。
消解王权崇高是不是必须消解、颠覆儒学崇高?这涉及对精英知识分子和儒家文化传统的互文性关联。新历史主义文学选择让沉默的小人物为庞大的历史发声,这是拉近历史和大众关系的有效方式,但也容易陷入虚无主义的陷阱。毕竟历史过于沉重,在既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原则,又不过于依赖作家主观想象的情况下,个别虚构的小人物很难真正承载我们想要找寻的历史背后人类价值的重量。
在这种情况下,郭启宏以古代精英文人的痛苦入手,一改文化精英高高在上的俯瞰地位,展示他们坎坷的人生际遇和精神苦痛,以他们在儒家传统文化中身不由己的崇高悲剧精神,打开了精英文学在大众文化包围圈里的突围缺口,实现了精英文学在“现代性”视域下新的启蒙的一种。话剧《李白》取得的巨大成功,说明在“现代性”的众多挑战下,精英文学仍然在耐心地追求光明,我们仍然需要精英文学。著名剧作家曹禺看完《李白》后,赠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这是对郭启宏写作笔力和创作视野的高度肯定。
当看到年逾六十的李白步履蹒跚请缨从军,舞台上站着的仿佛不再是李白,而是一张张看不清楚的脸面,月色婆娑中,有影影绰绰的人格恍惚其间——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纵然潇洒飘然如大诗人李白,肩上也扛着儒家文化的精神重担,在兼济与独善、入仕与退隐之间徘徊,他既藐视权位,又热衷功名,既身有傲骨不能屈,又有着“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媚态。站在坦荡荡与常戚戚间的,是作者面对李白灵魂的新方式。
郭启宏遵循着一种尊灵魂的写作方式,他一直试图写出人性的困难,以及人生阴暗面里藏着的真情。关于儒家文化精神重担下中国文人的曲与直,他无心刻意批判其中的善恶是非,而只是将精神的、人生的、带有神思的部分通过创造召唤出来,让观众聆听那些灵魂的对话或独白。
三、对知识分子人生价值的追寻和叩问
郭启宏的很多作品都对人的异化以及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进行了叩问。话剧《知己》具有代表性。该剧虽然以“知己”为名,但重点并没有停留在友情上,而是表现他们在遭受人生摧残时人格、灵魂和追求所发生的变化。对此,郭启宏倾注了无限哀恸和悲悯。
顾贞观为营救流放宁古塔的好友吴兆骞,忍辱负重在明珠府里坐馆二十几年,孰料千辛万苦救回来的人,早已在风霜刀剑的环境里,由一身傲骨的血性男儿,蜕变成了唯唯诺诺溜须拍马的麻木小人。昔日知己已然神形两异,这让他大受打击。对此,云姬安慰他,说吴兆骞能活着回来,就算是赢了。顾贞观发出了对文人人生价值的叩问:
是呀,世间万物谁个不为活着?蜘蛛结网,蚯蚓松土,为了活着;缸里金鱼摆尾,架上鹦鹉学舌,为了活着;密匝匝蚂蚁搬家,乱纷纷苍蝇争血,也是为了活着;满世界蜂忙蝶乱,牛奔马走,狗跳鸡飞,那一样不为活着?(忽然变色)可人生在世,只是为了活着?人,万物之灵长,亿万斯年修炼的形骸,天地间无与伦比的精魂,只是为了活着?(惨笑)读书人悬梁刺股、凿壁囊萤、博古通今、学究天人,只是为了活着?[9]
这段叩问可谓通达灵魂,直抵人心。是像真正的“人”一样有精神追求的活着,还是只留下生命的空壳苟活于世?从中引发出很多思考,例如,他们的浮沉际遇与“环境”“制度”等有哪些联系?他们的变化与权力者之间有哪些关系?他们身上一脉相承无法摆脱的劣根性和他们的生存又有什么关联?
关于《知己》,大多数人都将目光投射到了吴兆骞的身上,他是戏剧的剧眼。一个出场寥寥几次的人物,他的命运以及人格的演变过程,却主导着整部戏剧的走向。与顾贞观相比,吴兆骞的精神历程也使戏剧更加有深度、耐寻味——毕竟一定程度上他在宁古塔的境遇和选择,代表了普世意义上很多文人的内心挣扎。他的变节,引发了人们对摧毁文人精神支柱的东西的思考,揭示了时代和环境对人性造成的不可逆的伤害。
在吴兆骞身上,人性的悲哀、脆弱和荒谬昭然若揭,但是无论他在这部剧里的意义有多么重大,我们单纯把目光投射在他身上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单一描写精神的屈服感的作品太多了,这对于探究心灵、解释存在既有利也有弊,不过《知己》不同,它让我们感受苦难和恶意的同时,仍然葆有让人性站立起来的力量,这是顾贞观存在的意义,他的灵魂里有作者打量历史和生活时更仁慈和宽广的目光。如果说吴兆骞体现了郭启宏的敏锐和深刻,那么顾贞观则代表了作者对雄浑有力、悲悯包容的人格的肯定,他为一种有力量的人生和精神存在做证。
顾贞观对吴兆骞的营救,与西方荒诞派戏剧代表作《等待戈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与其说顾贞观在营救吴兆骞,不如说他也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等待戈多,未知中的坚持和等待本身就是意义所在。营救回来的吴兆骞,已经不是顾贞观印象里的吴兆骞。吴兆骞回来后视尊严于不顾的种种表现,有人耻笑他,有人斥责他,连吴的妹妹也对此感到不齿,但是,在戏剧的尾声,杏花天茶馆的茶客们又在对吴兆骞的势利和变节品头论足,众人哄然大笑之际,顾贞观表达了对吴兆骞的理解和宽容,他反问茶客们:“如果你我都在宁古塔,谁能保证自己不是畜牲?”[10]
这最后的追问延续了之前顾贞观对“活着”的叩问,发人深省,是将人的问询一步步推向极致的存在的思考。如果顾贞观也人云亦云一起抨击吴兆骞,失去了戏剧悲悯的情愫,那么人的灵魂境遇无疑就被简化了,对存在进一步的追问也就中断了,那么这部作品就难以获得深邃而博大的人类性的品格。这种追问以往我们在卡夫卡和加缪身上常常见到。无论是卡夫卡笔下的变异的甲虫、小动物,还是加缪笔下的反抗者西西弗,他们都有力地揭示出了人类存在中的异化、悖谬,以及无意义对人的粉碎,人类的灵魂赤裸裸地呈现其中无处藏身,也展示了一种对庸俗生活的抗拒。
顾贞观向存在、向灵魂发问的姿态,也是郭启宏的姿态。即使在绝望与荒凉的光景之中,纵然过程中或许也有摇摆动摇,但顾贞观还是会走向精神的极致,“我真羡慕那扑火的飞蛾,就是死了,也活得个辉煌!”[11]这是顾贞观的人生态度,尽管他没有真正做扑火的飞蛾,但他拒绝向那种无质量无尊严的生存妥协,纵然他为了营救友人像坐牢一样被困在明珠府里二十几年,但他仍然有着向灵魂发问的勇气和智慧,仍然有着 “吾日三省吾身”的清醒,仍然有着悲悯高远的心灵。他耗尽半生力气的营救结果是荒诞的,但是非在己得失不论,他的营救本身就是对荒诞的一种反抗。
顾贞观、李白这些“逆行者”的反抗过程充斥着满怀希望和不断失望的精神世界的隙缝和落差。他们在各种精神重担的挤压下上下求索痛苦不堪,被圈禁在冤屈的牢狱或被流放于荒凉偏远之地,越是反抗越是在荒谬的境地里无法自拔。郭启宏要求他们接受世界荒诞的本质。加缪在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中将荒诞定义为“人的呼唤和世界的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12]。剧中这些无处不在、挥之不去的荒谬和矛盾,渲染着反抗和救赎的迷惘和无望。但尽管如此,李白、顾贞观们依然一往直前,在绝望中永远心存希望,于消极中洋溢着昂扬的反抗斗志,在救赎与被救、自救中反复召唤精神与心灵的归属。他们时时刻刻以充满个性的呼唤对抗静寂、吊诡的外在世界,就像加缪笔下日复一日推动巨石的西西弗,忘情投身于徒劳与无望之中。郭启宏接受并正视世界和人生存在的荒谬性,并在严峻的“生之绝望”背景下,执着地阐述在荒谬的世界里怎样做“人”,如何把握当下生活、维护“人”自身的尊严。
郭启宏不止一次表达出对加缪的欣赏和喜爱。他曾说过,芥川龙之介、迪伦马特、加缪这三位作家的观念对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前两位作家,影响郭启宏更多的是关于历史与现实、写实与虚构等创作问题。而加缪提出的“人们可能拒绝整个历史,而又与繁星和大海的世界相协调”,从哲学角度影响到了他戏剧创作的精神层面[13]。中国知识分子对启蒙素来有着骨子里的执着,这也是郭启宏历史剧里知识分子自觉将自我与政治捆绑担负重任的形态之一种,实际上也是传统士大夫自我担负地对国家和社会责任的延续。对此,郭启宏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对现实生活进行体认,以同情与尊重的“人”的视角融入世俗生活,寻找历史和人情秩序的诗意存在。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救赎之旅。这种精神救赎的审美内蕴并不苛求人的生存环境的好坏以及政治权力的道德与否,而是关注人性的内在品质,即人们在面对荒诞世界的无奈、迷惘所引发的绝望与孤独中,在外在救援失败情况下无望的、颓废的战栗和呐喊下,在繁复投入和自我拯救的过程中回答内心焦虑和期待的心灵际遇和自我完善。
无论是在戏剧还是在现实中,在虽败犹荣的战争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让人肃然起敬的痛苦和坚持,那是高贵庄严的人生。这也是郭启宏对知识分子人生价值的探寻和叩问。正是在这种探寻和追问中,郭启宏展现了知识分子的心灵挣扎轨迹,表达了历史语境中人对苦难境遇的承受能力,折射出他们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下对自身信念惊心动魄的捍卫姿态,于周而复始的失败中取得人性上的成功,回归内在精神世界的繁星与大海。
[基金项目:苏州市职业大学校级人才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育人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2205000006)阶段性研究成果;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人才培养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2SJYB1623)研究成果]
[1]吴秀明 《从“启蒙的现代性”到“现代性的启蒙”——精英文学“历史化”的逻辑发展与谱系考察》,《文艺争鸣》2020年第9期。
[2]钟鸣《郭启宏评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页。
[3][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5 页。
[4]许纪霖《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三——道统学统与政统》,《读书》1994 年第 5 期。
[5]郭启宏《李白》,《郭启宏文集 戏剧编》第一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
[6]巴金《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页。
[7]郭启宏《李白》,《郭启宏文集 戏剧编》第一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
[8]杨绛《将饮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85页。
[9][10] [11]郭启宏《知己》,《郭启宏文集 戏剧编》第一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33页、第440页、第433页。
[12][法]加缪《西西弗神话》,杜小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13]陶璐《在“流转”中追求艺术创作的自由——访剧作家郭启宏》,《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5期。
(作者单位:苏州市职业大学 党委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