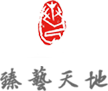
文艺评论
Comments
杨 宇
摘 要:自海勒斯开始电子文学“类型学”研究以来,西方学界在基本接受其结论的同时,一方面以雷特伯格的“体裁”研究为代表,继续回溯电子文学的发展史,寻找其隐藏的文学和艺术基因;另一方面以弗洛雷斯的三个“世代”划分为代表,对海勒斯研究中的局限性及时修正,表现出和当代媒介同步的理论敏感度。然而,上述两种分类方法都存在确定性和开放性的矛盾,作为替代方案的异质元主导分析法,更多的是在描述电子文学类型的属性特征,并可能取消类型学研究的多元性,以更具概括性的“技术+文学”式命名法终结对电子文学分类的尝试。
关键词:电子文学;体裁;异质元
引 言
学界对电子文学的类型学研究源于海勒斯(N.Katherine Hayles)在《电子文学:文学的新视野》(Electronic Literature: New Horizons for the Literary)一书中的尝试。面对电子文学对传统写作的冲击,海勒斯开宗明义地指出,“电子文学通常被认为不包括已经数字化的印刷文学,与之相应的是‘数字诞生’,是在计算机上创建的数字对象,通常是为了在计算机上阅读”[1]。对此,海勒斯将早期主要由文本块链接构成的超文本小说等视为“经典/第一代(classical/first-generation)”作品,而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多模态作品视为“后现代/第二代(postmodern/second-generation)”[2]作品。应当说,海勒斯当初的划分是合适的,尤其是她精准地认识到网络时代的到来对电子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以斯科特·雷特伯格(Scott Rettberg)、莱昂纳多·弗洛雷斯(Leonardo Flores)为代表的学者不仅将电子文学的历史上推至20世纪50年代,还进一步细化了海勒斯所谓的“第二代”作品的类型特征。
一、斯科特·雷特伯格的体裁分类法
雷特伯格从“体裁(genre)”入手,将电子文学分为组合诗学、超文本小说、交互小说和其他类游戏形式、动态和交互诗歌以及网络写作等多种形式。至于随数字空间技术发展而形成的定位叙事、互动装置艺术、虚拟和增强现实艺术等新流派,雷特伯格则以“支流(divergent streams)”为名在书中最后一章集中讨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所谓的“支流”并不重要,相反它们是“传统艺术媒体和学科之间界限消失的绝佳例证。这些形式代表了叙事和诗学未来的实验趋势”[3]。
当现代计算机因为数字编程而成为“元媒介”时,体裁便成为学院派所采用的一种迷人但略显过时的研究策略。如果说前互联网时代的电子文学还能勉强借鉴传统分类法,那么网络时代的电子文学对体裁的挑战则是全面而深刻的。当然,在技术产生电子文学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改变电子文学中的技术条件,二者共同形成一个反馈循环机制。比如,从指导接受者如何参与其中,到因消费媒介的出现而使接受变得简单,正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降低了电子文学的阅读门槛,进而使阅读不再成为一种认知实践,倒更像是一种潜意识的数字行为。对此,雷特伯格提醒我们,“界面既是作家创作过程的媒介,也是读者对作品体验过程的媒介”[4]。虽然电子文学至今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因其混合的马赛克性质而难以直接分类,雷特伯格采用体裁分析法只是出于简化电子文学史的目的,这样可以“为读者提供一套工具,使他们能够理解‘如何阅读’,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数字写作新形式”[5]。概括而言,雷特伯格主要从各体裁的发展脉络和技术要件这两个方面勾勒出电子文学的演进史。
首先,雷特伯格的处理策略并不是简单地以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为划分标准,而是在更广阔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下寻找电子文学体裁的艺术基因。虽然超文本小说是最早为学界所注意到的电子文学体例,但计算机技术与文学的最早相遇则发生在组合诗歌领域。从时间上看,克里斯托弗·斯特拉奇(Christopher Strachey)于1952年开发的“情书生成器”是首个用于生成文学文本的计算机程序,而从艺术和文学背景的角度来看,组合写作可以上溯到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法国“潜能文学工作场(Oulipo)”的先锋实验中。在探讨超文本先驱时,雷特伯格认为后现代主义启发了超文本小说从线性叙事向多线性叙事的转变,并在作品中突出拼贴、仿作和混搭的叙事技巧。并且,后现代文学中的“元小说(metafiction)”和“反思性(reflexivity)”特征,也是超文本体裁的重要关注点。“事实上,超文本作为数字媒体原生文学表达形式的第一种形式,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便是提供了‘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的文学记录”[6]。
第二,从数字原生角度来看,交互小说和网络写作则是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兴起的电子文学体裁。雷特伯格指出,交互小说“直接源于为个人电脑制作的最早的一些游戏,即20 世纪80年代的‘文本冒险(text adventure)’游戏”[7],而“网络写作是专门为互联网创作和出版的电子文学”[8]。互联网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媒介,尤其是开源运动和社交平台的崛起,使得电子文学的创作和接受门槛进一步降低。但恰恰是在这种“日用而不自觉”的网络环境下,电子文学通过有意的写作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陌生化的网络体验,不断提醒着我们应当对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保持着批判的视角。当然,网络写作也具有大众文化的属性,例如“分布式叙述(distributed narrative)”“跨媒体叙述(transmedia narratives)”“替代现实游戏(alternate reality gaming)”等,不仅扩容了电子文学作家们的工具库,也为这种本来先锋的文学实验增加了娱乐的喜剧色彩。或许,电子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可玩耍的文本”,至于这种玩耍性是走向独立的批判还是集体的狂欢,则不仅取决于艺术家个人的哲学立场,更取决于网络大众的解释策略。
二、莱昂纳多·弗洛雷斯的世代分类法
弗洛雷斯的研究起点是对海勒斯“经典/当代”划分原则的修正。在《第三代电子文学》(Third-Generation Electronic Literature)[9]一文中,他分析了所谓第二代、第三代电子文学的不同特征,将视角拉回更为现实的社交文化中。弗洛雷斯仍然将互联网技术出现之前的作品视为第一代电子文学,但随着网络的普及,电子文学进入了第二代发展时期,多媒体创作软件的发展为电子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个人电脑和网络进行创作和发布创意作品。此外,专业性的学术团体“电子文学组织(Electronic Literature Organization, ELO)”也于1999年在芝加哥创立。第三代电子文学充分利用社交网络和基于平台开发的应用程序,如Instagram、Twine、Unity、JavaScript等,进一步推动了创作技术的民主化,并将电子文学从先锋艺术推进了大众文化的怀抱。当然,前两个世代的电子文学流派在这一时期仍然存在,并以Twine游戏、Twitter机器人、Instagram诗歌、GIF和图像表情包等新形式焕发新生。
与海勒斯的“经典/当代”二分法相比,弗洛雷斯重点分析了互联网时代电子文学的类型和特征。首先,从生产所采用的技术类型来看,第二代电子文学往往追求形式上的创新,艺术家们的目标是尽最大努力创作出能体现技术原创性的作品;而第三代电子文学则更倾向于利用已有的技术平台,设计者不刻意追求生产过程的复杂性,更希望通过公布源代码使作品能在技术社区内升级和再生产,并通过社交平台实现作品的大范围传播。在第二代作品中,例如艾米丽·肖特(Emily Short)的《伽拉忒亚》(Galatea),不仅需要读者在网上下载包含作品的软件,还需要在体验过程中探索如何与非玩家角色互动,最好能理解程序员在作品编程中预设的个性。弗洛雷斯认为,第二代电子文学作品的技术特性会导致读者的接受难度增大,因此设计者会在作品中嵌入必要的操作指引或具有提示性的文本,而千差万别的作品界面在产生电子文学差异性的同时,更突破了我们基于经验的阅读期待。于是,每一次启动作品都是偶然的阅读事件,都需要现象学意义上的“悬置”,我们不会遇到相似的体裁,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努力学习“如何阅读”。换言之,第二代作品依赖“观众走向作品”才能完成。与之相比,很多第三代作品在界面和操作上都显得更加“友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出现在社交平台上的文学机器人,在ELO发布的第3卷《电子文学作品集》中就有专门的“机器人(BOTS)”子类。此外,像Vimeo、YouTube等网站上广泛传播的GIF图像和动态排版等网络模因元素也正在成为电子文学的新类型,它们充分利用了移动平台的技术优势,成功实现了跨设备间的混合和传播。
在电子文学的创作上,同一作者可能同时创作第二代、第三代作品,或者是出于保存和更新作品的目的,对之前的项目进行适时升级。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第二代作品体现出数字现代主义的气质,而第三代作品则更多地体现出后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的特征。对第二代作品而言,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创作即出版”成为现实,一种反抗性的礼物经济在电子文学社区内弥漫,而第三代电子文学作家探索出在学术团体和商业平台之外的实践形式。对此,弗洛雷斯以鲁皮·考尔(Rupi Kaur)、朗·利夫(Lang Leav)和罗伯特·M·德雷克(Robert M. Drake)为例,指出“他们纸质出版的Instagram诗歌集并不在应用商店销售,但有力证明了电子文学商业价值的潜力”[10]。凭借这种复兴印刷出版的尝试,第三代电子文学家绕过了学术组织的认可,以一种后现代的文化方式成功将流量“变现”。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作家们不再追求接受层面上的困难美学,而更看重艺术的易传播性。当一个庞大的粉丝群体崛起后,作家和大众便可以通过自助出版等形式探索出更符合社交文化的经济模式。
虽然“世代”的划分蕴含了时间的线性逻辑,但这并不代表着第一代和第二代电子文学作品的消亡,更不意味着第三代作品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具有合法的“先进性”。准确地说,当代电子文学是上述三个世代的集合,即使第一代作品越来越少,但只要创作者愿意,仍然可以选择使用那些颇具历史年代感的软件。
三、异质元主导的替代方案
虽然雷特伯格和弗洛雷斯的类型学研究在具体思路上存在差异,但我们仍能从中发现一些主流分类法的共性。在雷特伯格等人的研究中,暗含技术、文化在时间上呈正相关发展的趋势。客观上来说,这种研究思路上的二分法有助于将最时髦的创新和最独立的个体相勾连,从而有利于学界迅速将电子文学理论化和制度化。但正是这种妥协的立场使得对电子文学的研究“并没有提供唯一或最直接的途径来了解数字文化的诗学、伦理学、政治学和技术”[11]。总体来看,主流的分类研究往往从某一确定的维度出发,以此再探讨具体作品的不同特征,这种寻找类型普遍性的努力使得不同类型之间存在明显的裂隙,而现实的艺术实践往往是多种类型的复合。因此,有学者提出“基于异质元的主导”[12]分析法。所谓异质元,指的是由两种相对元素构成的特征组,而多个异质元又会构成一个分析矩阵,其中能决定结构属性的是异质元中占主导地位的元素间互相博弈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对电子文学的类型学研究,可能不再有明确的线索可循,而更像是在一个点状网络中寻找可能的连线。
(一)认识论/本体论
在雷特伯格和弗洛雷斯的研究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轨迹,但二者都没有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根本特征进行比较,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认为,能够体现艺术先锋性的电子文学作品与现代主义具有更直接的精神共鸣,而第三代作品则更倾向于后现代的解构策略。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内涵辨析不是本文所要面对的问题域,在此我们采用美国学者布莱恩· 麦哈尔(Brian Mchale)的结论,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时间上的划分概念,而是一种诗学组织体系的当代反映,“前缀‘后(post)’,在这里强调的是逻辑和历史的运动结果,不是纯粹的时间后置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延续,而不是对‘现代’的延续”[13]。
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现代主义诗学的主导性特质。通过对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小说《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 Absalom)进行分析,麦哈尔认为“现代主义小说的主导是认识论”[14],这种诗学关注主体在世界中的位置是什么、世界对主体有哪些是可知的,以及如何知道和解释可知世界等其他认识论问题;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主导是本体论,其所采用的策略是将“后认知之类的问题卷入其中,并将其置于前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在其中要做什么?我的哪一个自我要做这件事?”[15]这种本体论主导的诗学不仅关注文学文本的本体论,还涉及透过文本表现出的世界本体论。
如果我们把麦哈尔的“认识论/本体论”的诗学异质元用于对电子文学的类型分析,就会发现,“前网络时代、第一代作品,例如《下午,一个故事》(Afternoon:A Story)的认识论模式与Twine平台上的第三代作品,比如佐埃·奎恩(Zoë Quinn)的《抑郁探索》(Depression Quest)有着共同之处”[16]。换言之,弗洛雷斯的世代至少在认识论诗学模式下并不成立。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电子文学类型学研究中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替换为认识论诗学、本体论诗学,更需要结合电子文学本身的阅读经验来分析上述异质元的体现和影响。无论是认识论诗学还是本体论诗学都能产生文本的复杂性,但前者在电子文学中通过技术手段进一步提升了接受的难度,甚至导致一种挫折美学,而后者由于网络时代和平台经济的崛起,更倾向于创造一种易于传播的作品。或许可以说,任何一种电子文学作品都具有认识论/本体论的异质元素,出于不同的创作经验和主观体验,任何作品的“可供性(affordance)”都不相同。出于理论分析的必要,我们可以在“认识论/本体论”的异质元中找寻主导因素,但对于一种复杂的艺术实践,二者的递归操作才是推动电子文学类型学变化的动力之一。
(二)迭代性/联想性
如果说“认识论/本体论”这一异质元是从印刷文学引申出的分析框架,那么“迭代性/联想性”则完全建立在计算机文本的生成和阅读机制上。对生成文本而言,例如各类诗歌生成器和推特上的机器人,读者阅读的符号实际上是文本迭代生成的结果,这不仅和数据、算法的质量有关,还和读者的指令有关。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选择收录在ELO《电子文学作品集》第4卷中的生成诗歌作品《醉咏诗》(Zui Yong Shi)为例进行分析。在ELO编选的电子文学作品中,《醉咏诗》是难得的中文作品,其作者杨仁(Ren Yang)是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媒体艺术家。从作品形态来看,《醉咏诗》是一部界面和操作都很简单的多媒介作品,初始界面只有“拍案叫绝(regenerate)”一个启动键,而工作界面的主内容则是由程序随机生成的一首五言绝句,并同时播放根据平仄和五声阶旋律创作的背景音乐,但视听元素的出现只是对读者跟随作品开口诵读或吟唱的邀约。《醉咏诗》的创作灵感来自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以清代宫廷画家冷枚的同名画作为底板,很好地衬托出古人“欢饮达旦”“歌以咏志”的诗酒情怀。作品以李白的文本构建小规模语料库,并结合五言绝句的句法规范设置文字迭代的排列组合原则,使用Javascript语言编码,并通过p5.js和Rita等简单的工具库增加图像互动和语言处理能力,其效果是数据库中的词条将根据定时序列和读者对文的干预进行解析和重组。
虽然《醉咏诗》在技术和界面上都不复杂,但它很好地体现了我们所要讨论的迭代/联想异质元。首先,任何电子文学的生成文本都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语料库的质量决定了文本生成的文学质量,当然也决定了文本所能呈现的风格倾向。对作者而言,作品的设计实际上是建立在对源文本阅读基础上的迭代性“写作”,如果再考虑源文本中可能出现的典故、引用和改写等特殊手法,那么一般意义上的文本累积和生成理论在电子文学中并没有过时,甚至是通过现代计算手段得以发扬光大。换言之,技术步骤上的语料选择和数据库构建,在电子文学理论中可以看成设计者、源文本之间凭借“阅读/写作”相互转化以生成“作者意图”的初始环节。看似随机生成的文本或许并不是无意义的符号组合结果,而更像是一个被预设的复杂性互文系统,暗示着源文本、作者话语和数字程序的无尽意义链。甚至可以说,电子文学的生成文本也是以往所有文学实践的延续,它“将存在的文本和虚拟的文本都置于一个连续体中,其中每个文本的出现都会增加现有的文字符号层。人机中介只是书写和阅读行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另一种形式”[17]。
其次,就文本生成的技术路径而言,无论是根据语法规则的经验主义,还是基于概率的统计预测,甚至是当下自然语言大模型的机器学习,数字文化深刻地干扰了产生意义的叙事模式,通过编程规则、数据库结构、神经网络处理等“事件”的相互作用,计算机程序在数量上几乎可以生成语言组合的所有可能性。与此同时,电子文学中多模态的聚合效应增强了意义的虚拟性,并指向超越传统视觉和心灵体验的具身性参与,从而创造出一种更立体、更多元的联想氛围。人机交互使机器生成的文本与读者的点击相对应,并导致符号化和解释过程的事件性和表演性。通过重新排列诗行,读者可以干扰自动生成的文本层和语音文件的循环序列,他们的眼睛和触觉产生一种数据库的感官体验,重新演绎了文本的动态特性和写作的时空结构。
(三)沉浸式/互动式
从审美效果上来说,沉浸并不为电子文学所特有。在印刷文学中,读者将视觉元素的时间流动转化为思维的空间运动,以想象的方式来获得沉浸式的体验。实际上,无论是沉浸中的文本中心,还是互动所唤醒的现实主体,都在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中为数字艺术提供了技术空间。
我们以收录在ELO《电子文学作品集》第4卷中的《200座城堡》(200 Castles)为例,尝试分析电子文学中沉浸/互动的异质元特征。《200座城堡》由加拿大艺术家凯特琳·费舍尔(Caitlin Fisher)设计,读者利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摄像头扫描配套印刷册上的标记物,可触发那些叠加在印刷册图片上的音频和3D动画,从而在插曲式和非线性叙事中感受到一种神奇的感觉。这部作品最早设计于2009年,并在巴黎国家图书馆首展,收录进《电子文学作品集》中的是费舍尔2014年针对Apple iPhone和iPad操作系统更新的适配版。
正如《200座城堡》展示的那样,电子文学中的沉浸感与设备之间具有密切关系,最基础的是通过三维显示消除投影平面,其3D效果的质量取决于屏显所能达到的信息深度和广度,前者主要是指显示器的分辨率和图形处理算法的优劣,而后者可被定义为“同时呈现的感官维度的数量”[18]。虽然在《200座城堡》中还存在工艺实物的印刷册和作为技术载体的触屏设备,以至于我们无法否认纸张、像素等具体符号的中介作用,但从表面呼之欲出的动画和音频,已预示了虚拟现实最重要的特征,即界面的消失。换言之,我们渴望电子文学所要实现的革命性变化不是文学媒介的机器化,更不是赋予文学机器人格化特征,因为语言文字本就是人类所独有的智能媒介,而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文学媒介的透明化,至于这种透明化是“复活”了口传文学的史诗品格,还是再现了本雅明所谓的“讲故事的人”,甚至是走向文学终结的“后人类”,我们似乎都难以确论。如今,机器已能响应自然语言命令,键盘也变得多余,取代屏幕界面的是Apple Vision Pro中环绕用户的视觉显示。种种迹象表明,电子文学沉浸感的尽头是“一个后文字的时代,人们不再需要通过语言描述和语义游戏来传达个人观点、历史事件或技术信息。在这种没有符号的语言中,思想也将彼此透明化”[19]。
正因如此,我们还不能忘记电子文学中的交互功能。在早期的超文本小说中,这种交互性体现为一种弱文本交互,即读者通过激活可能的链接选择阅读顺序,但就整体的超文本阅读来看,即便是链接中断了沉浸的连续性,它和传统文本的阅读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质的区别。为了提升交互的密集性,设计者往往会增加链接的数量,但过于分散的链接又会导致阅读的断裂感和交互功能的失灵。对此,我们需要一种更加积极的强文本互动,它“允许用户创造符号,在用户的输入被视为虚构世界中的参与和行动时,互动性才能与沉浸感相结合,并实现对读者的赋权”[20]。与弱互动中存在过多链接的弊端一样,强互动也面临如何控制读者参与率的问题,但电子文学中沉浸与互动的冲突更应被视为一种挑战而不是限制。例如,在“空间定位叙事(Locative Narratives)”中,受众通过全球定位系统(GPS)在现实空间中导航,并随着位置的变化而阅读故事的片段,“当传感器在接受者的肢体动作、手势和模仿以及语言符号之间起中介作用时,真实世界的空间和文学的诗意便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相互关系之中”[21]。
(四)特定性/一般性
以上讨论的三组异质元并非针对数据操作技术而言,但电子文学和传统文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生产手段的数字化,因此我们还有必要从电子文学的独特性出发,探讨技术类型对电子文学类型学的影响。在编程中,数据类型定义了程序中数据的存储和处理方式。根据待处理的数据类型不同,俄国学者马诺维奇(Lev Manovich)将数据操作技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针对特定类型数据的媒体创建、操作和访问技术;第二类是能够处理一般数据的新软件技术(即不针对特定媒体),因此可称为独立于媒介的技术。”[22]
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看,特定媒介的数据操作技术似乎更容易被接受,因为传统上每种艺术形式都要有确定的载体,文学来源于语言文字,绘画是平面的艺术,电影虽然包含多种媒介但也是有限的综合。就像装置艺术破除了对特定媒介的执着一样,独立于媒介的数据操作技术对电子文学的影响在当下日益明显,它将我们的研究视角从媒介物质性转向软件研究。从形态上说,绝大多数的当代电子文学作品都是一种软件:从软件的本质特性出发,电子文学主要是一种应用软件,而基本不涉及系统软件和中间件;从软件运行的环境和平台出发,桌面软件、移动软件和网络软件都是电子文学常见的表现形式;从处理的数据类型和用途出发,电子文学中的多模态文本需要设计者广泛运用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处理软件。还需注意的是,通用软件技术的发展将文艺生产的技术环境从人脑和身体中脱离出来,它通过一系列诸如可搜索、可链接、可编辑等独立媒介技术降低了创新门槛,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复兴,构建属于“体力、智力自由发挥,手工、脑工人人平等”[23]的新型文艺理论值得我们继续探索。
特定性/一般性还为具体作品的命名提供了操作办法。在ELO编选的《电子文学作品集》中,每一卷都对收录的作品元数据、副文本、注释、操作系统等有清晰的说明。受此启发,学者瑞哈姆· 霍斯尼(Reham Hosny)提出用“文件扩展名+类似体裁”的方法来扩展文学分类器,他将电子文学系统可分为数据(data)层、处理(process)层和表现(presentation)层:数据层是构成文学空间的文字、图像、视频等的集合,处理层通过数据来开发文本的表现形式,而“文件扩展名是任何作品三层构成要素的一个可靠且合格的标识符”[24]。虽然,霍斯尼的命名法并不是一种广义的分类策略,而更像是服务于类型研究的便签,但通过“文件扩展名+类似体裁”的命名法,我们可以直观地判断出具体作品的数字特征和文学特征,而这恰恰是构成电子文学实体的核心元素。例如,在霍斯尼的分析中,他将阿拉伯艺术家尼斯玛· 罗什迪(Nissmah Roshdy)的作品《棋盘游戏》(La'eb Al-Nard)定义为“.mp4诗歌”。“.mp4”的扩展名意味着作品的数据包含有图像、动画、音频、文字等多成分,我们还可以此细化作品的音视频编码过程以及播放所采用的系统环境,而“诗歌”体裁的界定则源于作品是对前人诗歌文本的改写。
结 语
从体系上来说,雷特伯格、弗洛雷斯的类型学研究较为全面和成熟,又加之他们二人都兼具学者和媒介艺术家的身份,因此“体裁”“世代”分类法也就在学界更容易被注意和接受。虽然本文介绍了主导分析法的补充方案,但占据主导地位的异质元本身是开放的,包括但绝不仅限于我们已经讨论的四种:认识论/本体论、迭代性/联想性、沉浸式/互动式、特定性/一般性。随着技术和实践的发展,本文所探讨的异质元目录也必将会更新,甚至会出现多种异质元之间的均衡,从而取消所谓“主导”地位的结构意义。果真如此,对电子文学的类型研究也将不会存在,我们所能知道的便只能是对具体作品的命名。
[1][2]Hayles N. Katherine, Electronic Literature: New Horizons for the Literary, Indiana: Norte Dame,2008, p. 3, p. 5.
[3][4][5][6][7][8]Rettberg Scott, Electronic Litera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9,p.183,p.12,p.11,p.61,p.87,p.152.
[9][10]Flores Leonardo, “Third Generation Electronic Literature”,in Electronic Book Review,7 April 2019, https://doi.org/10.7273/axyj-3574.
[11]Ghosal Torsa, “Introduction: Global Literary Studies and Digital Literature”, in Ghosal Torsa, ed. Global Perspectives on Digital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p. 6.
[12][16]Mariusz Pisarski, “Diverse Mappings of Electronic Literature Expanding the Canon(s)”, in Ghosal Torsa, ed. Global Perspectives on Digital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p. 41, p. 42.
[13][14][15] McHale Brian, Postmodernist Fi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4,p.5, p.9, p. 10.
[17]Portela Manuel, Scripting Reading Motions: The Codex and the Computer as Self-Reflexive Machin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p. 198.
[18][19][20]Ryan Marie-Laure, “Immersion vs. Interactivity: Virtual Reality and Literary Theory”, SubStance, 28(1999), p. 117, p. 120, p. 125.
[21]Schäfer Jörgen and Gendolla Peter, “Introduction”, in Jörgen Schäfer et al. eds. Beyond the Screen: Transformations of Literary Structures, Interfaces and Genres,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0, p. 13.
[22]Manovich Lev,Software Takes Command,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 117.
[23]刘方喜《脑工解放时代来临:人工智能文化生产工艺学批判》,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页。
[24]Hosny Reham,“Classifying the Unclassifiable: Genres of Electronic Literature”, in Electronic Book Review,10 September 2023,https://doi.org/10.7273/kpt5-4p57.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