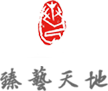
文艺评论
Comm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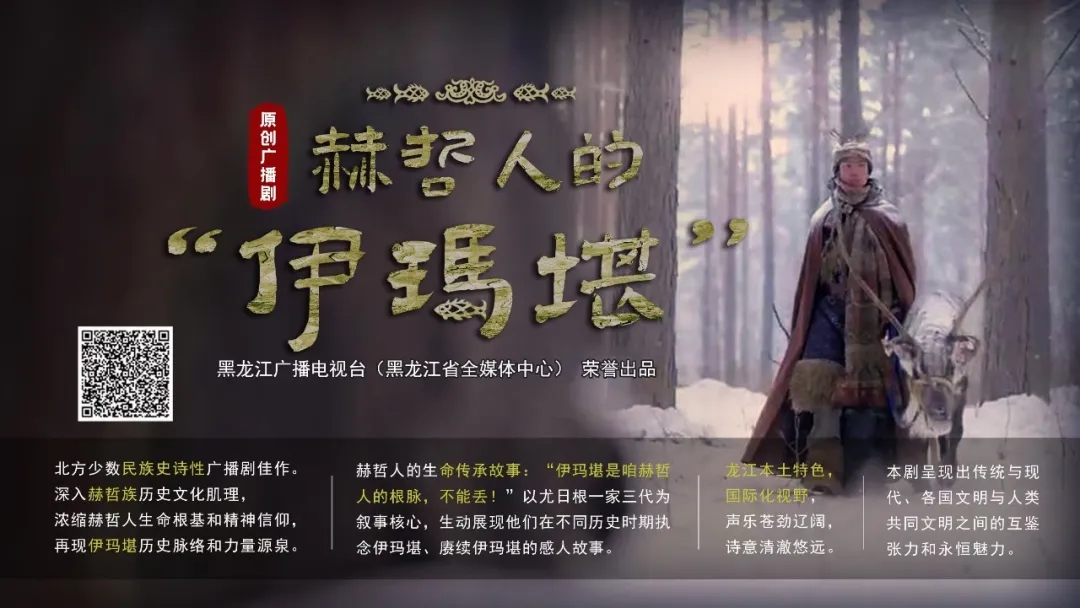
一部北方少数民族非遗史诗的生命之歌
——评原创广播剧《赫哲人的“伊玛堪”》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凝结着中华民族的独特智慧和文化精髓,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2016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黑龙江省同江市八岔村赫哲族群众,赞扬赫哲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特别是“伊玛堪”说唱很有韵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此可见,讲好少数民族赓续历史文脉,见证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命实践,是新时代文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光荣使命。
如何传承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让少数民族非遗故事“飞入寻常百姓家”,感受它的生命活力和时代气息,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制作的原创广播剧《赫哲人的“伊玛堪”》,开始了一次高水准的艺术实践。
一“听”一“见”重说伊玛堪
广播剧《赫哲人的“伊玛堪”》讲述的是北方少数民族赫哲族民族史诗伊玛堪的传承故事。赫哲族是中国东北地区一支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是全国六小少数民族之一,人口只有5000多人。伊玛堪作为赫哲族世代传承的古老民间说唱艺术,是赫哲人的生命智慧和生活经验的结晶,记录了渔猎民族的生命光华,被联合国列入《急需保护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定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的《乌苏里船歌》,就是由伊玛堪小调《狩猎的哥哥回来了》改编而成。随着时代变迁和赫哲语语言环境的逐渐消失,伊玛堪这一古老的说唱艺术形式,正濒临失传的严重危机。20世纪50年代至今,能够演唱伊玛堪的歌手数量急剧下降,且大多只能传唱两三个伊玛堪片段,因此,保护传承传播伊玛堪的任务刻不容缓。
为了挽救濒临失传的伊玛堪,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创作团队深入赫哲族居住地,探究该民族历史文化肌理,以赫哲人尤日根一家三代为叙事核心,生动地展现了他们在不同历史阶段下对伊玛堪的坚守和传承。在历经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时序变迁中,尤日根始终坚守“伊玛堪是咱赫哲人的根脉,不能丢!”的祖训,不停把伊玛堪蕴含的精神信仰传给族人。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儿子尤满江拒学伊玛堪,为了创收,竟违法炸江鱼,前来劝阻的母亲海珠沉船离世。尤日根一怒之下把儿子赶出家门,自己也八年未摸鱼皮鼓。母亲的离世使满江顿然悔过,开始自学伊玛堪,领悟伊玛堪的真谛,终于用行动得到父亲的原谅,拜父学真传,并把伊玛堪祖训运用到公司管理上,带领赫哲村成功致富。孙女尤胡萨代表中国到加拿大进行世界民族文化交流演出,引起广泛关注。
《赫哲人的“伊玛堪”》选材独特,立意高远,既有龙江本土特色,又具备国际化视野,声乐苍劲辽阔,诗意清澈悠远,是一部带给听众独特审美享受的史诗性广播剧佳作。全剧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浓缩了赫哲人的生命根基、精神信仰,不仅再现了伊玛堪原创发展的历史脉络、力量源泉,更让听众与剧中人一起生出对伊玛堪价值的深刻认同感。当全剧在学习强国、“中国广播剧研究会”、极光新闻、喜马拉雅等平台全网上线后,立即获得听众点赞好评。
“一核三线”打开伊玛堪的生命空间
广播剧《赫哲人的“伊玛堪”》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在全景式呈现伊玛堪延续的历程中完成的。全剧把人物和事件放置到五个历史时期,从赫哲人与历史、与生活、与时代、与世界的关系中,来塑造人物性格,并赋能伊玛堪说唱艺术生命价值、斗争精神、生存意志,以及为争取幸福生活而创新传承伊玛堪精神的文化自觉性。
全剧按照“一核三线”的人物关系塑造形象。“一核”指尤日根传承伊玛堪的经历,是全剧叙事的动力源,围绕他的坚韧、自豪、失落、忧伤、责任、保护、发展等所作所为展开。“三线”指尤日根与传承对象之间的关联和冲突:“一线”指尤日根与师父葛常胜的生死传承,师父作为抗联地下工作者,是从历史走来的赫哲人精气神的代表,他把传承重担交给尤日根,是生死托付,也是伊玛堪能否“活态”传承的转折点;“二线”指尤日根与家庭成员的传承关系,主要集中在儿子认为伊玛堪过时而不接传,后来父子和解,儿子用伊玛堪精神理念指导管理带民致富,这是现实关系;“三线”指尤日根与村民、与社会各种人际关系,除了血缘传承,更有各级组织单位的社会广泛传承,这是实践关系。全剧借“一核三线”交响式(父亲口耳亲传、代表中国走上世界舞台交流)、同构式(讲习所传、子孙转化性传承,在实践中化解创新矛盾)的表达,凸显出伊玛堪的精神凝聚力量和赫哲人从生命中自觉守护英雄史诗的内在动力,向听众传递出赫哲人的伊玛堪为人类共同精神家园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师父葛常胜是赋予伊玛堪历史厚重感的民族英雄形象,在与敌寇战火和生存灾难中经受考验,代表了赫哲人意志坚定,舍命保脉,永不放弃的精神蕴意;尤日根是新中国伊玛堪传播者的形象,他把传承伊玛堪与个人的生存价值、爱情婚姻、捕鱼生产相结合,表现了赫哲人迈入新社会生活实践,赓续伊玛堪英雄史诗的勇气和积极主动的生命精神。就是在深陷丧妻之痛时,也没忘记师父嘱咐,保护着伊玛堪,直到儿子醒悟认父为师,政府组织开办文化站,办起传习所、艺术团、出书翻译、参加国际非遗交流活动等,他将历经沧桑的伊玛堪深情地传给年轻人,并欣慰地看到它得以传承;儿子尤满江在经历了丧母之痛后,开始自学伊玛堪,以实际行动学传创新伊玛堪,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化新型传承者的形象。如果说尤日根代表的是贯穿全剧的核心伊玛堪意象,那么与时代共舞的最新意象便是尤满江和孙女尤胡萨。
充满生活气息的“诗意”伊玛堪
伊玛堪是赫哲人的生命镜像。全剧以尤日根讲述为视角,从个体人生到少数民族群体,从自然生灵到民族静态符号,从主体人传承到改变生活,介绍族人与伊玛堪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史诗性的叙事方式,为听众充分打开富有生命情趣的伊玛堪。
其一,巧设对话体,创造时空交错的戏剧空间。让现实中活态传承人尤日根与历史对话、与生活对话,将听众感受苦难中牺牲的民族英雄,幸福岁月的赫哲人间,不同时空生命场景的叠加变化,重述伊玛堪那永不枯萎的生命源动力。海珠美丽温柔勤劳,是尤日根传承伊玛堪的知音,她以母亲的身份保护渔业资源沉江而死,也是伊玛堪里的英雄。尤日根深情、海珠温情,俩人对话代表两个不同空间,俩人看似唠思念,实是围绕伊玛堪的生存成长诉说内心的担忧和希望,记忆里那些发生在不同时空的人和事,借着对话,存活在人们的记忆中,夫妻一问一答,内心一动一静,时光凝固,挚爱深情,诗意弥漫,仿佛是现实与历史一同在相互凝视,延展了诗意的叙事空间,增强了史诗性叙事的现代意味。对话体,是拓展新时代非遗传承的链接方式,是声音作品对非遗传承的独特表达。
其二,非遗符号嵌入听觉场景中,从生活细节中歌颂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增强价值认同。当代传承人胡萨说,伊玛堪跟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一样珍贵。全剧把具有代表性的仪式、才艺展示、服饰、器物、口琴、渔猎工具、渔业养殖等等,都通过生活的具体场景,用演播和音乐音效表现出来。如在加拿大受到特别关注的“空康吉”乐器演奏,就代表中国非遗参加了国际巡演。这些代表伊玛堪实物类的文化符号,听众看不见,却从人与物的互动中认识到它的文化功能和精神内涵。广播剧是听觉艺术,调动伊玛堪文化符号的塑造,能唤醒源源不断地传承意识和能量。
其三,化伊玛堪箭垛式人物为现代形象。特定情境下人物身份、情感元素直接转化为戏剧元素,让听众“听”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如尤日根同一场景下由愤怒的家长转为权威的传艺师父,由农民(打渔人)变为传习所所长,表现他作为新社会第一代传承人几经波折起伏,依旧矢志不渝;而海珠的形象具有文化“象征体”的意义,她在记忆的历史场景中是赫哲族文化的母体,在现实场景是知音、见证者,尤日根与她的隔空对话,既让思念满怀真挚,又让历史与现实适时碰撞且充满诗意;胡萨是年轻学者的代表,高学历,有专业,在世界舞台代表中国亮相,是少数民族非遗传承发展的希望;只有尤满江作为传承者是成长的形象,剧中重点塑造了满江觉醒转变后,不仅牢记伊玛堪真传,还将之活学活用于致富实践之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历史赎罪,带头引领赫哲人向未来发展,这是本剧赋予尤满江形象的独特而深刻的思想价值和审美特质。
其四,创造诗意的有声空间,突出赫哲人创造非遗生命的主体价值。剧情开始,三个“部落”阴森凶险混乱的场景,是对濒临被亡族灭种气氛的营造,象征着赫哲族种族生命及伊玛堪精神财富双重价值的深重危机,葛常胜用伊玛堪唤醒、引领族人顽强抗争,与抗联携手拼命守护,体现出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而与自然界和谐共生,感恩黑熊、怀念灵性“海东青”、鱼皮鼓和鱼皮衣展示、参加“乌日贡”大会等等,皆是以生命热情投入其中。伊玛堪作为文化产品,已经从非遗的“物——人——文化”互动,升华为赫哲人及各族人集体认同的文化价值,它的文化根脉早已深扎在赫哲人的心上。最后用远方传来海东青“雪爪”的鸣叫声,赞美了伊玛堪在新时代焕发出的生命活力。
心灵与天地共鸣的伊玛堪
广播剧能否成功走进现代大众审美视阈,离不开精美的演播、音乐、音效和剪辑。广播剧《赫哲人的“伊玛堪”》中,配音演员从主题入手,用与角色匹配度极高的声音塑造形象,细化人物的细微情感变化,将外在的神情气韵与内在的心理变化高度融合,使每个人物形象鲜活饱满。如主要人物葛常胜英勇果决、机智灵活、急促流利的东北方言;尤日根精细坚定、有温情有情怀有爱心的询问、承诺、愤怒、开怀;尤满江急躁、胆大,勇于接受失败修正错误,为民做主;海珠温柔能干、善解人意、心灵手巧,甜美细腻;就连次要人物樱桃、胡萨、傅站长、吴树林、小东青、翻译官等,角色的分辨度也是极高的,尤其是气声、哭声、伴声、远处混声,还有不同场景下同一人物声带的变化,声音的区分度很到位,强化了故事情节的整体性、生动性。
背景音乐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成为剧情推进和转场不可替代的叙事元素。如表现北方的自然环境,背景声音元素非常丰富,风声、水声、野兽声、鸟声、林涛声、划桨声,以及神鸟掠过天空的鸣叫声、地面鸡叫声、人和动物的混杂声,营造出少数民族地域特有的辽阔、苍远、悲怆、激情、欢愉的宏大场景,构成了充满神秘感和传奇性色彩的和谐画面,增强了全景式、史诗性展示赫哲族伊玛堪的文化特征。值得称道的是,音乐为全剧定下了调性,主旋律以《乌苏里船歌》作为全剧的氛围音乐,根据不同情境,分别改用不同的配声,男女合唱呼唤力量,抒发了赫哲人生活安定和幸福的内心感受,直到最后主题歌《永远的“伊玛堪”》响起,为这部时代的广播交响,献上了最温暖深情的祝福。
综上所述,原创广播剧《赫哲人的“伊玛堪”》是一部气势恢宏、充盈着史诗意味的精品佳作,让听众在一场声音盛宴中感知赫哲人在时光荏苒和社会变化中的生命追求,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对梦想和幸福的无限向往,以及赫哲伊玛堪在传统与现代、各国文明与人类共同文明之间的互鉴张力和永恒魅力。该剧的推出,不仅是对赫哲文化的一次深刻诠释,更是对伊玛堪保护与传承的深情呼唤。
(本文作者:李英姿,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文学伦理学研究所特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