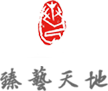
文艺评论
Comments
韩模永 潘 婷
摘 要:当下青年群体围绕“肯德基疯狂星期四”展开的文本内容,似乎已经聚合成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疯四文学”。从迷因视角出发对“疯四文学”的文本特征进行考量,发现它通常与热点事件拼接且呈现反转叙事的特征,极其强势的表现力正是它能作为强势迷因被受众广泛接受和激情创作的关键所在。“疯四文学”的生产逻辑在于,其契合了当代青年群体于现实压力下追求娱乐及宣泄情绪的心理需求,这也是他们积极呈现幽默自我和构建身份认同的过程。同时,借助星期四的时间节点,“疯四文学”拥有可持续性的生命周期,以供网友们在无厘头的文本中创造狂欢仪式。
关键词:“疯四文学”;迷因;肯德基疯狂星期四
“疯四文学”全名为“疯狂星期四文学”,源于肯德基品牌每周四举行的“疯狂星期四”活动。2018年8月,为了同麦当劳“88会员节”进行抗衡,肯德基首次推出“疯狂星期四”特价活动,主推售价仅为9.9元的鸡块、薯条等产品,但宣传效果不尽人意,“疯狂星期四”只被当作普通的活动日看待,其全网知名度并不算高。直到2021年5月,网友偶然发出文案:看看你那垂头丧气的样,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肯德基疯狂星期四。前半段狗血的台词和后半段意外的收尾,无意间引爆了网友们的创作点。此时的UGC内容仅仅呈现为简单句式的调侃,但“今天是疯狂星期四”这一有趣的反转表达已初露锋芒。之后的“疯四文学”内容和形式都愈发新颖,创作开始朝无厘头的方向发展。每到星期四,年轻的创作者们便开始编造各种脑洞大开的段子刷屏,引人入胜的前文+欧亨利式反转的模板开始成型,结尾总绕不开告诉读者“今天是肯德基疯狂星期四,V我50(微信转我50)请我吃”。“疯四文学”作为网络文化,展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较长的生命周期,目前为止,仅在微博话题中就拥有20.9亿次阅读数、420万讨论数的“肯德基疯狂星期四”,几乎涵盖了游戏、生活、情感等各个方面,无疑是继“凡尔赛文学”“废话文学”等网络热梗后新一波的迷因潮流。
那么,何为“迷因”?“迷因”音译自单词“meme”,意为“模仿的东西”。这一概念为理查德·道金森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率先提出,他大胆构想了人类文化领域中有着同基因(gene)一样的复制因子存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能通过模仿的方式进行自我复制从而实现传播[1]。之后迷因理论被语言学者广泛应用于文化研究,解释社会文化现象。如今,互联网对用户的行为模式产生深刻影响,更赋予了迷因新的形态和意义:那些在网络中得到疯狂模仿、复制和传播的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数字形式的文化片段,便是“网络迷因”[2]。正如同“疯四文学”一样,它们在经历病毒式浏览与分享后,充斥在日常生活中,这意味着新的流行文化诞生。通过迷因理论的视角,能够更深入地阐释“疯四文学”这一网络语言文化现象,揭示“疯四文学”究竟为创作者带来哪些价值才能让它受到如此大规模和长久性的追捧,而其他网络迷因却望尘莫及。
一、“疯四文学”的文本特征
互联网时代,网民们的创作力不容小觑,生产的信息浩瀚如海,而用户的精力又十分有限,哪些迷因能够脱颖而出并长久在网络中生存,也需要顺应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法则。“疯四文学”为能够长久生存和持续生产,常常选择用表现型方式呈现趣味怪诞的内容,又在形式上体现出复合结构的特征以增强传播力度。因此,在种种内容和形式的创新变异下,“疯四文学”于网络迷因的竞争中逐渐趋于强势。
(一)作为表现型迷因的“疯四文学”
学者布莱克摩尔在《谜米机器》中将迷因的类型区分为基因型迷因和表现型迷因两种[3]。基因型迷因指用户直接对迷因文本进行复制使用,一般不会对内容作出改动,从而产生同一意涵集群,比如“YYDS”“我真的会谢”“你是我的神”等。表现型迷因的创作空间相对较大,用户能够在保留迷因精髓的基础上,按照自身需求对内容或形式进行灵活添加或删改,使内涵更加丰富,从而与社会语境交互产生效果[4]。“疯四文学”能“经久不衰”,正是因其展现出表现型迷因的特征:内涵能随时空情景变化而无限扩展,且得益于自身无厘头和荒诞性的魅力,因此其内容即使再怪诞和扭曲,也常能得到充分理解。
作为表现型迷因,“疯四文学”最明显的特质体现在它拥有强大的变异空间,创作者可以将其嵌入到任意八卦热点、狗血爱情、悬疑推理等素材之中,创造出适用于各种社会语境的内容。“前天全部身家都压了阿根廷,昨晚借了高利贷压德国,现在的我身无分文,饥寒交迫,赌球不如吃KFC,谁能V我50,我想在这个冰冷的冬天吃上一顿疯狂星期四。”文案借助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热潮,成功吸引了用户注意力,甚至借助优惠活动的契机,创作者还大大方方说出“谁能请我去吃肯德基”,让自己“乞讨”的行为变得合理。在众多网络流行文化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疯四文学”凭借与时俱进的热点开头脱颖而出,博得用户的关注,使他们在强烈好奇心和八卦心的驱使下,完成对文本整体的阅读,在得知自己被愚弄后,产生趣味的情感共鸣。绝非完全复制,“疯四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层出不穷,正是如此,才保证了自身持久创新的生命力。
“疯四文学”的另一特点是它的无厘头和荒诞性,创作者无需过多考虑情理现实,甚至内容越与现实逻辑偏离则会越有趣味性,这也顺势强化了表现型迷因创作者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其他表现型迷因大多是依据主体自我需求而加工整合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创作者的社会生活现状,如“凡尔赛文学”是创作者对自我优越条件的炫耀,琼瑶剧般对话方式的“发疯文学”是为了让对方能感受到创作者现在的强烈情绪。而“疯四文学”的创作者并非重点想表达某种实际诉求,因此无需禁锢在真实语境中,这时描绘的场景则会变得不切实际。如“你好,我是奥特曼,我正在外星和敌人战斗!没有能量了!听说今天肯德基疯狂星期四,我现在需要有人给我带29.9块钱4个的吮指原味鸡补充能量,恢复后请你来外星做客。”创作者不可能是“奥特曼”,更不可能请阅读者“来外星做客”,但正是在这种离奇曲折的情境、跌宕起伏的情节中,读者才能在众多“离经叛道”的言语中识别出最“正常”、最核心的文案——“请我吃肯德基疯狂星期四”。这就是“疯四文学”表现出的与众不同的魅力:前后内容越是互不相关,与当下的现实情况越是不符,则越容易营造无厘头的幽默氛围。
除此之外,一些“疯四文学”的荒诞中往往又透露着现实的痕迹,且由于“疯四文学”诞生的媒介环境大多是基于熟人或半熟人的社交网络,读者会习惯性地将文案主体直接定位为创作者本人,因此亦真亦假的情节会让读者更加难以辨别其中的套路。“今天是我人生中最黑暗、最抑郁的时候,但是我很难把朋友当成垃圾桶或者树洞去倾诉,更喜欢憋着自己消化,睡一觉第二天醒来就好了,不想连累别人,不想把负面情绪传递给身边的朋友。但是,我更希望朋友能够给予我物质层面的帮助,今天是肯德基疯狂星期四,有哪个朋友愿意请我吃肯德基吗?”凭借现实生活中传收双方较强的社会关系,用户在看到开头时会疑问作者发生了什么事而选择耐心地对文本进行解读,直到结尾发现“KFC”“疯狂星期四”等“疯四文学”的标出性语言,才恍然大悟此文案与作者本人毫无联系,自己早已陷入友人设计好的“文案陷阱”。此时不论阅读者作出何种反应,可能顿感失语,也可能会心一笑,在“疯狂”的隐喻下,似乎所有的搞怪都有了合理性。
(二)作为迷因复合体的“疯四文学”
理查德·道金森在界定“迷因”一词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迷因复合体”的概念。有学者表示,迷因具有独立和复合结构之分,“迷因既能呈现为简易、单纯的一个独立迷因,也能呈现为由诸多单一迷因融合而成的一个独立的迷因复合体”[5]。相对于单个迷因而言,迷因复合体具有更大的传播性和更强的生命力。布莱克摩尔则指出,迷因只有依附“文化集合体”才能得到大范围的传播,即迷因必须与其他形式的文化广泛结合[6]。同进化论的观点些许相似,迷因处在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之中,各个迷因之间既是斗争又是相互联合的关系。为提升自身的生存能力,单个迷因之间彼此协作、互相融入变异成为新的迷因复合体,这将原本分离散落的独立迷因创作者聚集,实现彼此之间的感染,更容易激发对新迷因的创作和传播行为。
“疯四文学”迷因呈现出典型的复合体结构特征。它的文本并没有固定的创作格式,凡是能传递“今天是肯德基疯狂星期四”的意义、具备“读者看了这么久的文案最后被戏耍”的娱乐叙事功能的文本,都能成为“疯四文学”创作的素材。基于这种“没有固定标准”的标准,“疯四文学”的语用场景范围广,重组与扩展的空间大, 因此不同迷因的创作群体能通过融入自己的主观意识,在凸显“肯德基疯狂星期四”存在的同时又展现出另一迷因的特性,为它在不同群体间的和谐传播奠定基础。如有网友将动漫《名侦探柯南》中耳熟能详的人物台词与疯狂星期四结合,“你好,我是高中生侦探工藤新一,我刚在游乐场被打晕,被黑衣组织强迫灌下了APTX -4869,现在身体竟然变成了小孩子,听说疯狂星期四黄金鸡块有奇效,希望大家能V我50,助我一臂之力”。两种迷因巧妙地组合让文本妙趣横生,也更容易让关注此动漫的群体受到“疯四文学”的感染。无论另一迷因为何,“疯四文学”总能轻松实现与它的完美嫁接,这不仅仅是内容的相互组合,也是主体间的相互聚合。这种结合的自由度是其余网络迷因难以逾越的,也是“疯四文学”生存能力强大和持久的关键。
于是,前后原属不同领域的迷因通过复合形式诞生的“疯四文学”,其文本也极易呈现出戏谑和反转的特点。“戏谑”是“疯四文学”创作的核心理念,对原初文本的戏仿、对时事热点的恶搞、将多重元素拼贴等都是戏谑的展现,而“反转”意味着打破常规,是对传统叙事秩序的挑战,更是将戏谑的语言转化为幽默逻辑的动力。“老师问三个学生,用什么东西可以填满整个房间。第一个学生找来稻草铺满地板,老师摇了摇头;第二个学生找来蜡烛点燃,屋子里充满了光,老师还是摇了摇头,因为学生的影子没有被照到;这时第三个学生拿出肯德基疯狂星期四藤椒无骨大鸡柳,顿时香味充满了整个房间……”读者或许正按传统思路,把它当作一则正经的师生教育故事进行阅读,却不料后文直接来了个反转,打破了这种常规的想象,让读者啼笑皆非。在戏谑和反转叙事下,用户将原本互不相干的迷因文本组合,初始文本的主题、符号都被重新解构,各要素原有内涵均被消解,“疯四文学”系统中构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意味。最终,在“整蛊”他人后带来创作者自身的愉悦以及为阅读者带来的欢乐,逐渐成为新时代年轻人的审美趣味。
(三)作为强势迷因的“疯四文学”
在网络迷因生存和竞争的过程中,能够被用户注意、记住并且得到大量复制和传播的迷因则被称为强势迷因。道金斯指出衡量强势迷因的三个标准,即多产性、长寿性和保真度。多产性指迷因被复制和传播的频率高、速度快且范围广,长寿性指迷因的结构并不易被复杂的外在环境摧毁,也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消失,这也意味着强势迷因具有稳定性和高保真度,在变化的过程中始终能维持自身原有的含义,并会在长期的使用之中逐步稳固地位。
其一,在各种网络流行语竞争激烈的今天,能得到频繁复制、广泛创作和传播的“疯四文学”无疑是具备多产性特征的强势迷因。带有戏谑、反转意味的叙事内容首先就是一大亮点,互联网进一步为它的创作和扩散提供了理想的传播介质。2021年12月底,肯德基官方注意到网络上关于“疯四文学”的创作趋势,借势举办了“疯四文学盛典”,从此正式将“疯四文学”IP化,助推全网娱乐风潮。同时,从微信朋友圈到微博超话,从知乎到B站到抖音,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上围绕热点进行内容创作的惯常做法,也鼓励了用户对“疯四文学”进行不同版本的再创作。肯德基官方亲自下场和社会化媒体平台双重助推,同时互联网提供源源不断的丰富素材,使“疯四文学”于流行文化和社会参与的碰撞之下擦出新奇的火花,进一步强化自身多产性的特点。
其二,相比其他网络迷因的昙花一现,“疯四文学”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互联网中海量的信息混合杂糅,以及人的记忆容量有限,使得迷因不可能全部被长时间记住,只有符合记忆规律方式展现的迷因才能被看见和使用。而网络迷因能够被记忆和生存的时间长短,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自身的重要性和重复率[7]。在重要性方面,起初,肯德基疯狂星期四只是具有迷因潜势的信息,但因其强势的表现力适用于各种传播语境,并契合大范围用户的心理意向,从而信息被复制成形式不同、内容变异的各种表征加以传播成为网络迷因;在重复率方面,乔纳•伯杰曾在《疯传》中提道:“诱因是信息能够得到大范围传播的深层次原因之一。”[8]这也是迷因得以高频率重复的关键因素,“疯四文学”之所以得到长久性的记忆,正是因为其具备诱因——它与“星期四”这种高频场景联系在一起,建立了一种潜意识的链接,能持续地、稳定地、高频地调动用户的记忆。随着更多主体加入到“疯四文学”中,会愈发绑定其与周四的联想。基于以上两种特点,“疯四文学”生存的时间比其他网络迷因更持久,长此以往加深了用户对它的印象和认可,从而更加频繁地在网络中对其使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疯四文学”的寿命。
其三,“疯四文学”为了更稳定地进行繁衍,会继承元迷因的基本性质和特征并保留精髓,即围绕“肯德基疯狂星期四”进行变异,以此来保证自身的复制忠实性。如“全员核酸检测通知——今日(9月29日,周四)进行全员核酸检测,检测时间、地点安排如下:1.检测时间:17:00—18:30;2.检测地点:肯德基大门口”。创作者突破最初的简单句式,与先前核酸检测的现实衔接,衍生出公告通知的形式,文案虽未直接引出“今天是肯德基疯狂星期四”,但它依旧继承着原初迷因的搞怪性质和与现实热点结合的特征,隐晦地用时间——“周四”、地点——“肯德基大门口”点明“疯四文学”的精髓。无论形式和内容如何变化,用户能够凭借对以往“疯四文学”的认识、理解和感受,在变异文本面前通过联想和类推,破译新形式中始终存在的关键要义——“肯德基疯狂星期四”。然而任何一种迷因文本都携带着大量的约定俗成,语用使用的背后蕴含着深层的社会认知和文化价值判断,这表明文本很有可能被用户的认知系统排斥,从而不被识别和破译。“疯四文学”的“准宿主”是那些能够准确识别“肯德基疯狂星期四”意味的群体,对于常常与网络流行文化接触的年轻人而言,他们早已建立了一个各种流行元素存在互通的迷因系统,“疯四文学”奇异另类的表现方式,能被他们轻松地识别、认可和记忆。最终,在维护高保真度的前提下,用户乐此不疲地对“疯四文学”进行改编,肯德基官方和媒体平台的大力渲染再次强化它的流行力度,使其不断在互联网中得到传播。
二、“疯四文学”的生产逻辑
“疯四文学”作为青年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体现青年群体独特另类的符号表达方式的同时,投射出其创作的价值理念,并凸显出社会关系的属性。其生产逻辑在于,“疯四文学”作为强势迷因符号被赋予了独特的情感意义,青年群体在参与创作和情绪宣泄的狂欢之中,塑造内心渴望的网络形象,并逐渐聚集为兴趣共同体从而获得群体认同。最终,“疯四文学”网络迷因得到广泛接纳和传播,成员们在每周四定期的意义互动中,形成一种新的仪式体验。
(一)参与创作和缓解压力的满足
“疯四文学”是典型的用户参与创作的成果,读者对文本叙事有更多的操控空间,互联网技术又进一步赋予读者对偏离文本原意想象内容的生产能力,这暗合了约翰·菲斯克文化快感理论的第一个层面:再生产的快感。菲斯克认为,流行文化的快感既来源于对原文本语境的辨识和对原文本内容的二次生产,也有对原文本与日常生活相关联所产生出意象的快感[9]。米歇尔·德赛都曾用“盗猎者”比喻积极阅读并对文本进行挪用的观者,还指出他们是“游牧民”,总是在不断向新文本迈进,挪用新素材,创造新意义。亨利·詹金斯援引这一概念,在《文本盗猎者》中提出“参与式文化”一词,认为读者在对文本进行阅读的同时,还运用挪用、拼接等特有的方式对媒介文本进行截取再组合。网络时代迷因传播的主体不能简单划分为创作者和阅读者两端,而应将每个个体视作活动的参与者,在“阅读—创作—分享”的循环过程中完成传受身份的交融,这一特性拓展了再生产和参与创作的内涵。因此,伴随互联网发展成长起来的青年群体既是“疯四文学”的阅读者也是创作者。出于猎奇心理和增进生活趣味的娱乐需求,用户作为文本解读者和意义加工者,更倾向于接受和生产幽默诙谐的内容。因此,即使知道这么戏剧性的文案避免不了“今天是肯德基疯狂星期四请V我50”的套路结尾,读者也依旧心甘情愿地从这之中获得创造性解读的满足,并将这种体验二次传播,由此形成再生产的快感[10]。在分享传播的过程中,阅读者完成了身份的转变,成为“疯四文学”的传播者甚至是创作者。他们熟练地借助不同媒介渠道对“疯四文学”进行模仿和改编,对“今天是肯德基疯狂星期四”的原含义进行挪用,对调侃和戏谑的意味进行盗猎,将本不重合的故事或热点与其拼贴,通过反转性的叙事模板创造出戏剧冲突,原文本变异成新的适用于不同交际语境的“疯四文学”。
在“疯四文学”迷因的生产过程中,创作者常常会有意偏离主流话语体系,通过追捧和模仿以示对现实压力的抵触,从而达到菲斯克快感理论的另一个层面:躲藏和抵抗的快感。吉登斯认为,现代人类生活中传统的“自然节律”,即随时间推移会产生周期性变化规律的人的体力、情绪和智力,已经被资本现代性建构出的“理性时间安排”所取代,时间成为一种商品被标注上了劳动和生产的价值,为与现代生活接轨,人类不得不严格遵从固定的时间秩序[11]。比如,现代秩序将七天划为一个周期,周一到周五默认是学习和工作的日子,循环往复。在韦伯看来,当人类长期陷入这种理性化的秩序之中,削弱了作为自然人的生命体验时,他们很容易产生忧郁的情绪。因此,人类期待拥有一定的自主娱乐空间来暂时躲避这种约束,放松压抑的心情和沉重的压力。我们长期麻木地处在“工作—休息—工作”的秩序之中,在经历前三天工作日的“折磨”,周四成为学生党和工作族对沉重任务最为厌烦以及对即将到来的娱乐日子期待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刻,因为再坚持一天,周六和周日便可以收获美好的休息时光。“疯狂星期四”为这种时间安排提供了喘息的机遇,每到星期四,它都在提醒我们,别忘在学习和工作之余抽出时间放松一下,和其他拥有类似精神状态的群体分享交流,通过对现代生活的调侃创造出仪式性的快乐。
实质上,“疯四文学”就是一场盛大的文化狂欢,以“上班族”和“学生党”为代表的青年群体便是其中的狂欢者。“疯四文学”为其提供了绝佳的减压窗口,供他们对外讽刺戏谑,对内自嘲调侃,借助疯狂的文案将自身剧烈的情绪波动或神经病一般地小题大作宣泄而出。网友们在荒诞的文本生产创造狂欢仪式,这也是“疯狂星期四”真正疯狂所在。
(二)幽默自我和趣缘群体的追求
在“疯四文学”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个体达成了一种理想的自我重现,形塑了一个新的网络形象。欧文•戈夫曼将社会看作是一个舞台,日常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其中的演员,人类的社会互动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了呈现自我而进行的理想化表演[12]。社交网络是不同主体交换信息和资源的载体,也是主体展现自我形象的场域,它的出现打破了自我呈现的技术限制,网民们能够在借助媒介进行情绪表达的同时进行深层次的意义生产和符号互动,信息的分享传播行为就是传播者主动建构自我意识和虚拟形象的社会行动。“疯四文学”的创作者们便是利用拟剧演绎的方式来呈现幽默风趣的自我:一方面,从“疯四文学”文本内容来看,创作者运用丰富多样的视听元素搭建剧本,通过无厘头的反转叙事制造幽默感来达到良好的表演效果,彰显自己脑洞大开的独特个性和媒介形象;另一方面,官方亲自下场举办“疯四文学盛典”,寻找原创“疯四文豪”,再次引导受众自我呈现的逻辑,鼓励构建“文豪”人设。于是,当在社交网络上生产“疯四文学”时,能够展现出创作者自身幽默有趣、脑洞无限的风格,这样的情感需求是创作者普遍存在的心理驱动力。
从宏观层面而言,“疯四文学”的创作者并非纯粹想要通过建立幽默的人设来标榜自己的独立个性,更重要的是在这过程中寻求趣缘群体的关注,从而获得极大认同感和归属感。互联网技术加持突破了时空区隔,兴趣作为标签凝聚了无数网络群体,寻求精神共鸣的网民们找到了新的联结方式。在微博、知乎等网络平台中有关“疯四文学”的话题,即是拥有同一文化取向的趣缘群体在网络空间中的文化再建[13]。而每一种文化迷因的流行和趣缘群体的兴起,都暗自预设了用户背后的身份,20~30岁为主的“学生党”和“打工仔”便构筑起了“疯四文学”的圈层体系,他们可以借疯狂发挥想象力的契机来释放压抑已久的学习压力、吐槽工作的不满。这也意味着,“疯四文学”早已超越娱乐本身,其广泛受到追捧和模仿更是因其契合了当下青年群体苦中作乐的心理状态。正是由于“疯四文学”拥有更深层的意义,其本身具有一定遮蔽性,能否解读出文本背后的深层含义,则取决于传收双方是否处于同一话语圈层。能与创作者拥有共通意义空间的个体,理解“疯四文学”中透露出的对繁重的学习或工作任务的自嘲和调侃,才能获得进入“疯四”圈层的“门票”。加入娱乐习性相似、品位爱好相投的集合体后,“疯四文学”帮助每个人识别彼此的精神底色,拥有同样生活经历的个人对其背后所代表的群体性特征再次产生情感共鸣,获得自我和群体确认的社会价值,从而进一步促进“疯四文学”的病毒式阅读和传播。
(三)定期疯狂与互动仪式体验
“疯四文学”既是释放内心创作激情和压抑情绪的载体,也是呈现自我以获得群体归属感的桥梁,传播者一系列围绕肯德基疯狂星期四的符号表达和社会互动,构成了仪式行为。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认为,传播是一种创造、修改、转变并共享文化的过程,可以将众人以共同体的形式凝结在一起[14]。即用户通过对某些符号进行加工创造,与其他成员互动交流产生共同信仰、聚集成为共同体,建构一个有文化意涵的世界,它强调传播的场景、参与的成员、成员间的互动及产生的意义。
首先,“场景”是传播仪式达成的必要条件之一。数字时代技术的快速更迭突破了以往学者认为仪式感构成的前提——物理空间的身体共同在场,互联网近乎实时对话的频率将不同实体空间的用户聚集到同一平台,无需亲身在场也能在彼此间传递情绪[15]。具体到“疯四文学”而言,每到周四,青年群体开始不约而同地在微博相关超话、微信朋友圈或是熟人建立的微信群等网络空间中分享“疯四”文案,交流过去发生的热点事件或是新发现的迷因形式。在这其中,“疯四文学”与特定时间场景的相关联也是仪式感外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它不仅为创作者们提供了文化狂欢的空间场域,也提供了暗示即将得到压力缓解的日期——星期四。大家渴望周四的到来,因为他们能从“疯四文学”的传播中体会到定期“发疯”或“吐槽”的快乐,正是这个特别的时间节点,进一步强化了成员的仪式体验;其次,“互动”是传播仪式的本质特征。由于“疯四文学”迷因强劲的冲击力和煽动性能轻易调动读者的互动热情,使他们通过点赞、评论、转发或是参与相关话题讨论的方式表达对内容的认可,这再次鼓励了成员的创作热情、刺激了成员的生产动力,并且互动又能反过来激发读者的模仿或二次创作行为,形成一种注重情感和自愿参与的组织形态,进一步带动“疯四文学”的仪式传播;再次,“意义”是传播仪式的核心要素,符号是其载体,情感是其内涵。“疯四文学”的符号被赋予了独特意义,用于表达成员的情感需求:一是来源于内心参与创作和缓解压力的渴望,二是青年群体对差异化网络形象的追求从未停歇,“疯四文学”能为他们塑造“文豪”人设提供机遇,并在此过程中帮助他们寻找到拥有相似趣味的共同体,从而获得群体归属感。
概而言之,“疯四文学”的创作者通过符号的创新变异来助推生产意义,在互动交流中吸引拥有共享意义的成员聚集,不断进行再加工和再传播,他们通过这种仪式感的参与维系着数字化时代的社会关系。可以说,通过场景、互动和意义联动达成的传播仪式体验,一定程度上正是“疯四文学”源源不断生产的内在逻辑。
三、“疯四文学”的价值反思
“疯四文学”迷因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创新,它反映出个人、群体甚至是现代社会的文化进步。当然,任何一种文化的创新发展都难以回避利与弊的交锋。青年群体企图通过“疯四文学”的传播寻找到治愈精神的蛰居处,因此他们容易迷失在群体参与、集体狂欢的快感之中。这实质上是内心孤独的症候,“疯四文学”成员间的仪式互动和群体狂欢,在网络空间仅表现为一种短暂的、虚拟的陪伴,这种狂欢仪式终究只是泡沫般的幻想。同时,在娱乐至上和消费主义的裹挟之下,“疯四文学”也难免会出现粗俗低劣的内容,以及呈现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当我们沉溺于躲避现实的快感享受之中,习惯性地用自我化、情绪宣泄式的话语表达,不仅会导致审美能力的退化,冲击语言的规范使用,还会逐渐丧失理性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另外,传播仪式的维持需要新鲜血液的流入和持续性内容的产出作为支撑,而“疯四文学”实质上多是无效信息的传达,这无疑是在消磨阅读者的时间和精力,并且不断地、重复地生产也让创作者感到精疲力竭,最终对文本的创作激情和对内容的情感共鸣逐渐消逝。生产动力缓缓消退,也意味着仪式生命也即将终止。我们可以用“疯四文学”短暂地调试生活,但始终要警惕它对人类结构性思考的消解,因为倦怠的精神会让我们难以对现实进行理性的思辨。
与其他的网络文化迷因不太一样的是,“疯四文学”还与肯德基品牌息息相关,它从最初的偶然出圈到后来成为官方品牌营销策略之一。但与其他营销方式有所不同,“疯四文学”的迷因营销并没有所谓的预热期、爆发期和平淡期,却成功让年轻群体和它分享了自己的私域社群,创作者们无意间成为自发性、无偿性并且乐在其中的品牌营销人员。并且“疯狂星期四”与每周固定的星期四时间节点紧密结合,这意味着“疯四文学”的生命周期是可持续性的,它能为肯德基带来源源不断的流量,这是其余竞争者无法突破的壁垒。但迷因营销归根结底是为了品牌盈利,肯德基的初衷是想借助“疯狂星期四”让产品本身触达用户,然而在“疯四文学”迷因的创作中,却很少有人涉及“肯德基疯狂星期四”活动具体的产品,受众并不能从各种二次创作中知晓肯德基哪些产品正在优惠、哪些产品值得购买。另外,当消费者打开“疯狂星期四”的活动又会发现,所谓的“优惠”其实都颇有门槛,“疯狂星期四”的价格并不够“疯狂”,营销声势再火爆,也逃不过消费者对产品本身的追求。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网络文学的媒介变革及空间转向”(2022SJZD135)的阶段性成果]
[1] [英]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卢允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2] 郭小宇、马静《互联网迷因研究:现状与展望》,《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年第6期。
[3] [英]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高申春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4] 常江、田浩《迷因理论视域下的短视频文化——基于抖音的个案研究》,《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12期。
[5] 何自然《语言中的模因》,《语言科学》2005年第6期。
[6] 夏德元、王宇博《模因论视域下短视频对外传播的媒介逻辑》,《新闻爱好者》2021年第1期。
[7] 何自然《流行语流行的模因论解读》,《山东外语教学》2014年第2期。
[8] [美]乔纳·伯杰《疯传:让你的产品、思想、行为像病毒一样入侵》,乔迪、王晋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第89页。
[9] 廖中鸣、胡江伟、姜小凌《狂欢、区隔与抵抗:游戏圈“梗”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5期。
[10]姜小凌、黄偲佳《仪式狂欢与消费快感:对网络低俗信息传播的再思考》,《西部学刊》2018年第11期。
[11]陈氚《现代性议题中的社会时间理论》,《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8期。
[12]苗存龙、徐茂华《青年“丧文化”的表征解析与引导路径》,《理论导刊》2022年第2期。
[13]雷婧妍、任健《场域理论下微博超话社区的网络趣缘群体关系研究》,《新闻爱好者》2022年第1期。
[14]闫伊默、刘玉《仪式传播:传播研究的文化视角》,《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5]胡哲君《社群、情感、仪式:数字营销时代的品牌传播》,《视听界》2018年第1期。
(作者单位: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