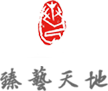
文艺评论
Comments
一
中国山水画讲究营造“天然图画”。天然漫无理则,要靠人的情感爬梳方可动人,所谓“春见山容,夏见山气,秋见山情,冬见山骨”。说是直书四季也行,说是借景抒情也可。陈从周先生满腹山水,谈山水始终不离一个“情”字。他说:“泪眼问花花不语”,痴也;解释“春风无限恨”,怨也。故游必有情,然后有兴,钟情山水,知己泉石,其审美与感受深浅,实与文化修养有关。不能品读山水则不能游山水,不能游山水则不能画山水!难怪他游小小一个十笏园,也得了“亭台虽小情无限,别有缠绵水石间”之句。
读出意趣,读出境界至关重要。意不太容易言传,等于品位、癖好之微妙,总是蕴含一点趣的神韵,属于纯主观的爱恶,玄虚不可方物,如声色之醉人,几乎不能理喻,是对人对事对物的即兴反应,毫无公式系统可套。这也是袁宏道所谓“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入理愈深,去趣愈远。情趣品位跟精神境界当然分不开,而因心造境是中国山水画的特点和灵魂。造境在于立意,立意又归于境界。自王维以诗入画,开启了中国画“无声诗”的境界。尽管时至今日,我们已看不到他的真迹,但后续者“无诗不能成画,无画不能成诗”。东坡先生有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心画境是中国画所追求的至高“境界”。董其昌说:“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画家的笔墨幽情,映象的是天地自然宇宙的诗心画影。一管毛笔,蘸上墨在宣纸上,留下线墨的轨迹,也留下画家的心迹。中国画的灵魂是“澄怀观道”描摹诗心、禅意的画境,在一片幽深静谧中呈现清澈澄明的禅心与空寂天籁,自然的和谐,画里画外,物我万象,融融一体。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从自然物境到纸上云烟,能把这种心境转化成山水艺术,需要的是修行、悟道和才能。这不仅仅是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更是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境界。难怪郑板桥在《沁园春》中,流露出情意绵绵而又怨气十足的人生体验,多了几分惆怅,亦多了几分风骨。
山水花月本无情,情在看山看水看花看月的心眼之中。宗少文卧游山水、王右军耽悦 浮鹅、米襄阳痴心拜石,说是“求趣”实际上也流露出他们对人性的无限体贴。现代人身在城中,心在城中,当以画幅为山水,以盆景为花圃,作卧游之想,培养自然情怀,籍此多少可以摆脱心中的围城。 自然山水还需用心去感悟,去品读,用画用诗用文写出来的纸上山水反而耐看耐读。陶渊明描写《桃花源记》的文章传诵至今,篇中刘高士怀揣美好的向往与执着的追求,在道途中尽情领略赏玩了一番,让寻仙境的梦想伴随至终,致使后来仿效者层出不穷。“桃花源”所以为人所慕,我以为不在其有无,而是自己尽享在路上追梦的过程,正如杜尚所说:“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的生活”。饱读纸上山水,可以读出自己胸中的山水,进而读出属于自己的那份自在、通达。世人真的不必再去寻觅“桃花源”了。
二
自有山水画以来,自然就是作画的内容,自然生画,画生白然。山水画以笔墨颜色构川壑,心中的自然与客观的自然,迹化为纸上云烟,让人一时说不清有我还是无我,或两者兼有。当江山随光阴变迁,兴衰荣枯,历尽沧桑,丹青逐年代辗转藏家,易宝遗珍,日久弥光。每每时光已逝,世事变迁,画仍溢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山水画呈现出一个人文的形态,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情境,从情感到境界无不演绎出多姿的图式趣味,一部山水画史居然是一部人文的历史。
当今山水画,因人制宜。生活方式的变化,科学文明的变革,为艺术经典的传承赋予了时尚精神。以传统鉴当代,以当代法传统,正是山水画的魅力之所在。山水画通过艺术手法,架构起一个精神生活的空间,使人与自然的融合,在“物我两忘”中得以实现。故而“峰峦之起伏、林木之稠薄、风雨之明晦、烟岚之隐现、泉瀑之缓急,虽山川依旧,而意常新矣”。这也是山水画对自然景观多层次内涵的诠释。
黄宾虹先生晚年居杭州栖霞岭,得山川之兴。其画“山川浑厚、草木华滋”,天地有被水气浸润过的味道。“山的阴影交割,树阴的投影,山川的温润厚重,土地的肥沃,万木的葱茏的生机,雨后的湿润,云气的蒸腾”,是他对自然的热爱在山水画境中的反映。
李可染先生到底是深明中国传统艺术意识和中国画家气节的大家。论山水画有“可贵者胆,所要者魂”八字,不仅涵盖了画艺的经验,兼且流露出画人的怀抱。每次听画家论画,想到的往往不是画,而是人。李可染先生《万山红遍》的色彩,可以是斜阳,也可以是爱国热血。中国画可贵者意,所要者识,意与识会,山水画当然不再是眼中单纯的山水画了。
无论是明艳或是淡远,它们都是具有灵性的。中国画有一个特点,同样的墨色深度,一遍给足和一层又一层积染,效果是不一样的。一遍给足者,浅薄而无层次。层层积染者,则画面墨韵清厚。“十日一山,五日一水",说的是对画面的苦心经营,也是表达心境的过程。在不厌其烦的层层皴擦点染中,天地流动的“浩然之气”降临到画家的性情中,活在了画面上。
傅抱石追承石涛,喜欢大写意地挥洒山水。他尤好酒后挥毫,有印日:“往往醉后”。在飞驰的酒意中,把各种皴法、树法、点法的连缀运用砸个粉碎。但正如风雨再大都有去势,它用明暗调子和有纵有紧的方法,确定了物象的结构层次,“大胆落笔、小心收拾”。在读它的画时,我们仿佛听到了天地放纵的声音而非噪音。
我与山水画,山水画与我。也如庄周梦蝶,蝶梦庄周。相和而嘈,相恰而合。从而再塑一个我,再画一张画。引自然造化于起居,扬艺术文化于生活。与其说是人对自然家园的思念,不如说是对风雅平和之精神乐园的眷恋。构筑人文的“家园”,疏别喧嚣,使心灵有块恬静的天地,也是我所向往的境界。凡事至于适度便是最好。当你意识到其实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生命和感情,有自己的一份生活的时候,就不会只是从单一的角度出发了,而会试图去寻求一个合适的方位和重量。营造一个纸上的“山水文章”,似乎那些历经丹青的明艳静远、味道的生发收放、声音的泼洒清平、性情的恬静放纵,直至意境与眼界、矛盾与适度、背离与回归……仿佛是一篇永远也品读不完的“山水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