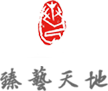
龙江代表性作品
LIBRARY OF LITERARY WOR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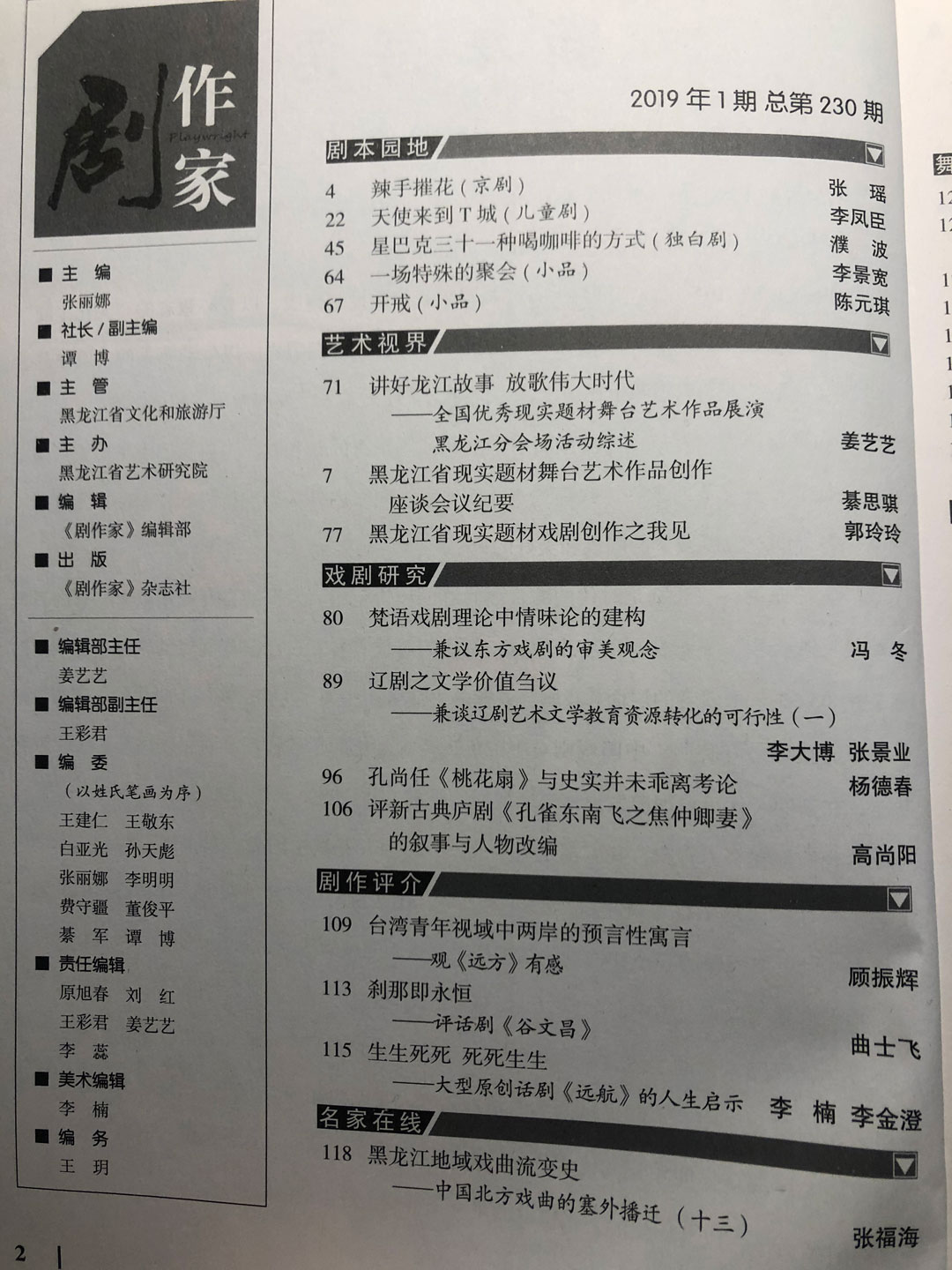
作者:郭玲林
作品:《黑龙江现实题材戏剧创作之我见》,《剧作家》,2019年1月。
黑龙江省现实题材戏剧创作之我见
郭玲玲
历时半个月的全国现实题材优秀剧目展演(黑龙江分会场)结束了,此次展演我省有龙江剧、话剧各四部,音乐剧、评剧以及皮影小戏组台各一部,共计十一场演出依次亮相。可以说,现实题材剧目的创作数量是可喜的,这也充分显示出我省各地市、各院团对题材的选择是有一定的时代敏感性的。但同时艺术质量的参差不齐,整体水准的相对较低以及内容和形式的雷同等等问题,也在此次展演中暴露无疑。目前,我省现实题材剧目的创作同全国各地的现实题材剧目的创作一样,存在很多问题,这其中既有共性的问题,也有我省自身特性的问题。
一、选材的局限性
展演的十部大型舞台戏剧作品中有五部是以扶贫攻坚为题材的,包括龙江剧《头雁》《这片黑土地》《扶贫书记》,话剧《情系双龙湾》《在路上》;两部以英模人物为原型的剧目分别是报告剧《金桂兰》和评剧《千里沃野》;以母爱为主题的音乐剧《非常爱》,以“生死”为主题的话剧《远航》,以艺人追梦为主题的龙江剧《九腔十八调》。我们注意到超过半数以上的戏在写扶贫,写英模人物,题材单一,内容相似,主题雷同。显然,我们的现实题材创作被局限在狭窄的视域内了,个人认为这是由于对现实题材的理解出现了偏颇。
“现实题材”的概念是田汉在1950年的第一次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在报告中提出的,这也是从国家文化政策的层面首次对艺术创作的题材提出的具体要求和指向性的引导。长久以来, 历史题材剧目几乎占据戏曲舞台全壁江山的现实,让大多数人在头脑中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传统戏曲特有的虚拟性表演程式更适合演绎遥远的历史题材,更适合表现远离现实生活的历史人物。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明确提出戏剧改革方针的会议上提出的“要对现实题材关注”的观点,给了现实题材创作以合理的政府推动力和明确的政策支持。显然,当时关注“现实题材”的导向是针对戏曲舞台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历史题材”为主要创作内容的思维定式而提出的。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现实题材呢?简而言之,一切能够反映现代社会生活状态、变化和发展的现实,都可以纳入到现实题材中去。由此可见,现实题材可以是大气磅礴的国家性事件,也可以是家长里短的个体性事件;可以是城市里的腐败贪婪,也可以是农村中的脱贫攻坚;可以是英模人物的形象具体,也可以是永恒话题的概括抽象。环视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它是多元的,多彩的,多层次的,有让我们始料未及的物质成就,还有让我们应接不暇的鲜活的人物和事迹,更有时代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猝不及防的观念的转变和思想的更新,这些都是我们现实题材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源泉,也都是能够、并且应该用戏剧的艺术形式去表现、去描摹、去挖掘、去反映的时代馈赠。
但现在在我们的戏剧舞台上却看不到多视角、宽领域、有深度的现实题材作品,满眼望去是看不尽的扶贫攻坚,数不清的英模人物和说不完的好人好事。诚然,这是我们的祖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奋斗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现实,它值得艺术家去关注、抒写和歌颂。但当全国仅以《扶贫书记》这四个字命名的剧作就高达50部之多的迷之撞车出现时,我们是否应该反思呢?目前现实题材的创作到底怎么了?它是不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入了一个误区?似乎,不以颂扬为落脚点的不是现实题材,不用力粉饰的不是现实题材,不以高大全的人物为主角的不是现实题材,不蹭热度的更不是现实题材……有这样的戏剧观念和对现实题材的误读,舞台上屡屡出现千篇一律的故事和似曾相识的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也有人说,难道这些不是现实吗?我不否认这是现实,也认同这还是我们新时代里最真切、最感人的现实,但如果仅仅将目光聚焦于此,那无疑是人为地缩小了现实题材的内涵,更切断了现实题材的外延。现实题材创作的意义在于艺术化地呈现时代面貌,挖掘时代的气质和精神。它的内涵很深刻,它的外延更为广阔,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现实题材等同于“主旋律”,确切地说,是等同于我们头脑中固有的、狭义的“主旋律”。其实如果我们的创作者能将“主旋律”的广义边界扩展到一切歌颂真、善、美的作品,那么现实题材的选材也就不会再如此单调、雷同和乏味了。大到政治、经济、外交,小到养老、教育、婚恋、改革、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太多可入戏的素材就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发生着、变化着,只要找好切入点,现实题材创作的舞台上定会百花齐放,处处芬芳。
二、定位的模糊性
此次展演中半数以上扶贫题材的剧目生动地再现了扶贫攻坚过程中那些感人至深的事件,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舍小家为大家的驻村扶贫干部形象,向观众们展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崭新的面貌,仿佛让观众们亲眼看到了那些脱贫致富的农民们的张张笑脸,也让扑面而来的欣喜感从舞台之上蔓延到了观众席间。可以看出参演的每一个院团都是在用心用力用情认真地作戏,竭尽全力用艺术的表现方式去提升作品的艺术质量,进而完成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使命。基层院团由于天然的地理优势,他们更了解扶贫攻坚道路上的困难,更能理解扶贫干部的牺牲奉献精神,更会为国家扶贫政策的深入贯彻执行感到振奋,没有人比他们更想将这一切呈现在舞台上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为之感动,为之兴奋,为之潸然泪下的了。尽管选择这样的题材不乏有政府导向因素的存在,但力求实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始终是每一个文艺团体的最高目标,这种努力在演出的细节中也是能够捕捉到的。
追求始终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归根到底,还是对此类现实题材创作的定位不准确,对“宣传品”和“艺术品”之间的区别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界定。无论是龙江剧还是话剧,甚至是报告剧、纪实剧,都应该以“艺术品”的标准去衡量和要求,以戏剧的基本特征去评判,以戏剧创作的基本规律为底线,以艺术的美学规范和观众的审美需求为落脚点。从戏剧的故事结构、情节设置、人物关系到矛盾冲突,都要合情合理,将生活的真实转化为艺术的真实,只有如此,戏剧所要表现的社会现实、想要表达的心灵诉求和力图传递的时代精神才能触动观众,直抵人心。也只有这样的艺术品才能承载宣传品的功能,因为无论何时,只有相信才能感动,也只有感动才能隽永。
院团生存的窘迫决定了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自主选择题材的自由,而克服重重困难最终立在舞台上的一部部主旋律的作品天然地被贴上了“宣传品”的标签,这是他们无可奈何的选择,也是这类文艺作品无可推卸的责任。但院团主体,包括所有主创团队的成员却不应该顶着这个“标签”去创作,而应该忽视它的宣传品出身,时刻牢记剧作只需“对艺术负责,对现实负责,对观众负责”。秉承这个原则去创作我们就会发现,最终的成品首先得是“艺术品”,而正因为它成其为艺术品,才实现了宣传品的作用。如果只是为了完成一项政治任务,将生活中的事件原封不动地罗列到舞台上,将宣传的口号和说教堆砌在舞台上,忽视戏剧性,忽视现代性,那它不仅不是艺术品,更无法完成宣传的任务。中国剧协副主席罗怀臻说过,“现实题材的作品不等同于快捷的宣传品,而是艺术品,它终归考验的是艺术家的原创力、想象力与表现力”【1】诚然,这样的题材创作难免会受到真人真事和行政干预的限制,但艺术工作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始终以艺术品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三、创作的模式化
近些年现实题材创作被业内专家和观众普遍诟病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明明是真人真事改编,为何搬到舞台上就不好看,不感人了呢?那是因为舞台上呈现的故事不真实,不可信,发生在人物身上的那些纠结和选择显得离这个时代的认知很远,无法引起“共情”,又何谈感动与宣传呢?笔者认为想要扭转这样的局面,最重要的是解决对现实主义的理解缺乏清晰认识这一根本问题。
提到现实题材就绕不过“现实主义”,那么,二者之间到底有着何种联系呢?仅从戏剧的角度来讲,狭义的现实主义,指的是文艺复兴之后的19世纪末出现的与浪漫主义相对的一种戏剧流派,它反映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生和真实的人性。广义的现实主义,则泛指文学艺术对自然和当代生活的复现和模仿,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手段。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都是还生活的本来面目,呈现和叙述生活”【1】,现实题材的创作要始终秉承现实主义的精神和追求。除了复刻生动的生活外,现实题材创作最重要的特质是要有烛照现实的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有对现实生活独特的感受和独到的见解。
罗怀臻曾经说过,“戏曲的现代性不是简单的时间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取向和品质认同。”取材于现实,来源于生活的创作并不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现实题材,只有其承载的价值观念具有现代性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现实题材。我们注意到在很多戏剧作品都会出现的相同的桥段:主人公在面对家庭与工作的两难选择时,无论是爱人分娩、孩子病重还是父母病危,都毫无意外的选择后者。其实,选择后者也并非不可,但一定要给出一个比前述事件更需要人物的合理理由,让选择理所当然,让人物真实可信。否则,人物做出的艰难决定就会让观众不信服,甚至觉得虚假、疏离。究其原因就是,这并非现代价值取向的产物,人物的行动找不到符合这个时代的心理动机,它离真实的生活太过遥远。这样的戏,即使台词够现代,舞台的手段和技术再现代,它也绝非严格意义下的现实题材作品,因为思想不具有现代性。
我们注意到这种创作模式化的倾向愈演愈烈。于是在现实题材创作的舞台上我们看到了很多雷同的故事和雷同的人物,即使是题材撞车,也不应该出现创作的相似。这其实是剧作家自身观念就没能完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就无法谈到对所选取题材所表现的社会现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了。现实题材的创作更要强调作者对生活的认知,创作者不是素材的搬运工,而是拥有现代意识、现代观念、现代审美和现代技术的艺术工匠,用匠人的精神打造出来的作品,才是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社会的优秀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