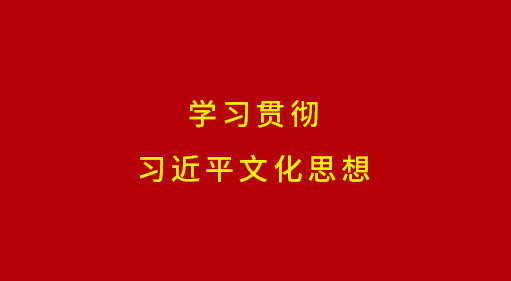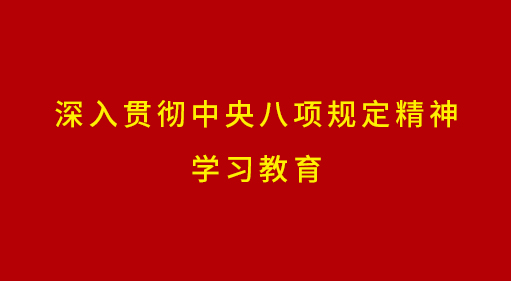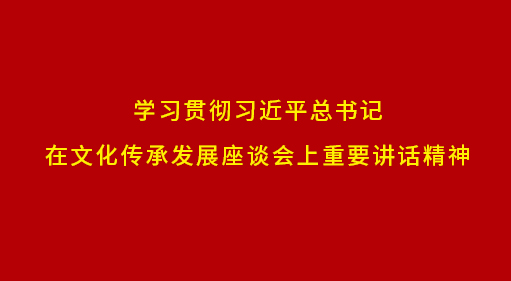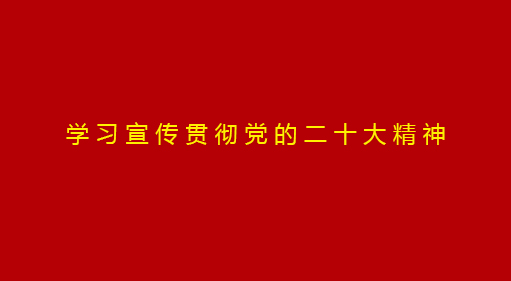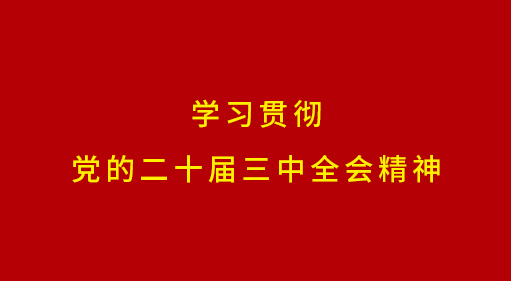景观再生与情感引渡:新大众文艺的媒介再造
时间:2025-08-07
郑 琴
摘 要:自文字媒介向数字媒介转型以来,大众实现了多元身份建构,大众文艺的内涵在意识形态与市场逻辑的交互作用下发生历史位移。媒介迭代既为大众文艺带来多元景观,也隐含着价值迷失的潜在危机。在新媒介时代语境中提出的新大众文艺,将“技术赋权”与“人民导向”的话语进行并置,通过情感共同体建立全新的阐释与对话路径。考察媒介与大众文艺的双向互动,有助于厘清大众文艺生成的内在规律,更为新大众文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历史镜鉴。
关键词:新大众文艺;媒介传播;文艺景观;情感共同体
新媒介时代的文艺生态变革,既构成了“新大众文艺”提出的历史语境,也是其理论建构的核心命题。2024年7月,《延河》杂志发表《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阐述了“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认为“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1]。该论述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两种阐释向度:一是通过考察网络文学、新媒体“短文学”等新兴文艺形态,揭示新媒介时代对文艺机制的重塑,例如南帆认为“‘新大众文艺’的提出是与‘新传媒时代’联系在一起的”[2],李震认为新大众文艺兴起的直接原因是“新兴数字媒介的日益普及化和智能化”[3];二是以打工文学、素人写作等文化实践为具体切片,勾勒大众从接受者向创作者的主体嬗变,例如《文艺报》指出,“在新大众文艺的浪潮中,素人写作者正成为新的创作主体”[4]。欧阳月姣认为作为新大众文艺重要例证的素人写作,实际是“文艺大众化”的当代回响,标志着从“为大众代言”到“大众自我言说”的主体转变[5]。无论是将媒介革命指认为新大众文艺的发生动因,还是将大众的角色变迁概括为其本质特点,诸种阐释虽侧重各异,却共同指向认识新大众文艺的前置条件:其一,在媒介的作用下,大众文艺发生了何种历史转换?其二,新媒介时代如何重构了文艺创作的图景?其三,置身于新媒介时代中的新大众文艺,将如何接续大众文艺的传统,又获得哪些现实的生长可能?对这些问题的现象追踪,不仅能对大众文艺实践进行系统梳理,也能在对文艺景观的深描中探究数字时代文艺转型的关键规律。
一、媒介与大众文艺的历史形态
文艺大众化一直是现当代文学史发展的关键线索,但媒介变革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论证。看似依附于技术发展的媒介,不是大众文艺的外部因素,而是内嵌于文艺生产的有机要素。它不仅是文艺创作与批评的物质载体,同时也是文本形态与大众角色的形塑力量。以媒介为线索勾勒大众文艺的历史形态,可以借此还原技术变革与文艺民主化的共振轨迹。
在文字媒介时代,“文艺大众化”的提出始于左翼作家的革命想象。左翼作家对“文艺大众化”的倡导,本质上是无产阶级对文化权力的争夺,他们希望以《大众文艺》等报刊为阵地,将“文艺大众化”建构为革命叙事的必要路径。在左翼作家看来,“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6]。这一构想与大众的知识能力现状形成悖论:一方面,长期被排斥在文字媒介之外的大众难以理解左翼知识分子的革命话语,导致其窄化为知识分子的语言改良实验;另一方面,左翼作家同步强调作家身份的大众化,认为“惟其由大众出身的作家,才能具有大众的意识,大众的生活感情;所以也只有他们才能表现大众所欲表现的东西”[7],而真正的大众又无法在短时间内突破文字媒介门槛。就大众的文化困境,鲁迅无奈地感慨道,“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8]。
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政治导向下,解放区文艺实践开启了跨媒介尝试。《讲话》确立了“普及”的优先性后,延安文艺作家转向街头诗、秧歌剧等相对浅显易懂的文艺形式,代表性案例是李季《王贵与李香香》对信天游的转化——诗人以形式转译重构阶级叙事,为农民群体提供自发传诵的革命教材,使政治话语成功渗透进民间文化。新中国文艺体制的建立,本质上是延安经验的延续。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重申“普及第一”,认为文艺工作者需要关注工农兵群众的文艺活动,指导“普及”的真正落实[9]。随着“普及”工作的深入展开,工农兵文艺工作发生了从“普及作品”到“培养作家”的拓展与延伸。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补充道,“我们必须一方面采取各种方式将专业作家、艺术家所创造的一切优秀作品普及到群众中去”,“另一方面,必须帮助他们通过业余活动方式进行自己的创作和表演,从这些活动中发现和培养劳动人民中的艺术天才”[10]。这一方针在地方文艺刊物中形成具体实践。以《长江文艺》为例,农民作家李文元向《长江文艺》寄去应征信后,《长江文艺》不仅刊发了李文元的信件与诗作,同时组织专栏“谈李文元的诗”,对李文元的创作提出针对性指导意见。在这一时期,“大众文艺”与“工农兵群众文艺”近乎是同义的。尽管“大众”获得成为文艺表现主体的可能,但其创作实践仍被收编在知识分子的“艺术指导”内。
在市场经济中,大众文学的概念逐渐被泛化。此前“大众往往被认为是‘革命’的推动力,是一个国家神话,它的等级是高于‘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学界“开始用‘城市’‘民间’‘新市民’等重新指称‘大众’这一概念”[11]。郁达夫在《大众文艺释名》一文中指出,“大众文艺”这一概念借用于日本流行的“大众小说”,原本“是指那种低级的迎合一般社会心理的通俗恋爱或武侠小说等”[12]。大众文艺的“降格”反映了其商品属性觉醒,尤其在1992年南方谈话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后,这一特征愈发显著。当严肃文学经历“文学失却轰动效应”的集体焦虑时,《废都》的巨额销量以及其带来的剧烈争议却使其成为“上个世纪末最大的文学事件”[13]。《废都》的出版与销售奇迹源自出版商对大众文化心理的精准把握,在文艺政策松绑与市场经济深化的作用下,长期被压抑的市民文化需求终于获得了合理的释放渠道。《废都》的“成功”消解了文字媒介作为严肃文学专属载体的精英属性,论证了其向大众文学生产工具转型的可行性。
互联网技术的迭代解构了文字媒介时代单向度的传播路径。1996年,金庸客栈的创立为网络文学提供了早期实验场域,但受制于较低的网络普及率,网络文学只能是小众爱好者的精神自留地。2003年,起点中文网推出“按章订阅”的VIP付费机制,催生出《斗罗大陆》等现象级长文本,推动网络文学向类型化创作发展。2010年前后,智能终端的普及促进了微信公众号、知乎等新媒体平台崛起,为读者带来新媒体“短文学”的阅读选择。但网络文学与新媒体“短文学”为大众定制生产的策略,同样加深了1990年代以来对大众文学商品化倾向的深层焦虑。王小峰曾悲观地表示,大众文化已然成为一种变现工具,制造者与受众已经“集体沦落成毫无审美情趣和判断标准的纯消费动物”[14]。这也在提示我们,既要看到媒介松动带来的机遇,同时要关注价值浮泛可能带来的危机。
数字媒介的出现为创作者带来“写作平权”,“从论坛时代到博客,再到今天的微博、微信和公众号造就的各种自媒体,全民写作成为可能”[15]。新大众文艺的首倡者《延河》编辑部也指出:“无论身份,不论阶层,门槛消弭,圈子打破,人人皆可为作者,老少皆可成博(播)主。”[16]准确来说,当创作门槛消弭、传播渠道开放,大众得以超越知识分子的中介角色,以创作者、传播者、评论者等多元身份参与文艺共建。但大众的主体性解放却伴随着大众文艺内涵的悖论性转向——大众在获取文艺民主的同时,大众文艺却正在经历通俗化、商业化的价值偏移。这又引出了更复杂的问题:当非职业化创作成为新媒介时代的显著特征,大众主导的文学实践是否仍能被纳入经典文学研究的观照范畴?回答这一追问,需要从当下的文艺景观入手,审视观念预设与实践发展之关系。
二、新媒介时代的文艺景观
从阅读的角度理解媒介的新旧之分,如果说“旧媒介”指的是“印刷媒介生成的纸质文本”,“新媒介”则包括通过电子屏幕显示信息的种种媒介[17]。互联网等技术的普及与发展开启了新媒介时代。新世纪初“严肃文学、网络文学和青春文学三足鼎立”的格局,随后演变为新时代文学语境下“严肃文学、网络文学和新媒体‘短文学’”的三元共生[18]。文学期刊通过学术话语的持续赋魅建构起严肃文学的审美圣殿,在与专业读者深度对话的同时,也与大众读者形成了天然的审美区隔。网络文学虽能借助类型化叙事与便捷的互动机制快速聚拢读者,但流量逻辑支配下的超长篇连载形态始终面临意义消解的危机。新媒体“短文学”虽精准适配当代社会的碎片化阅读场景,但其对瞬时传播效能的过度追逐,致使其难以在有限文本中进行深度叙事。简述这三种文学形态的媒介之便与其创作边界,有助于理解数字媒介如何将它们带入共生时期,并构造新的文艺景观。
严肃文学首先展现出积极的数字转向。当新媒体浪潮汹涌而来,文学期刊主动从封闭的纸质空间走向开放的移动终端。《人民文学》《文艺报》等文学期刊相继开通微信公众号,构建直达大众读者的传播通道。以数字转型的先锋样本《收获》为例,如果说《收获》的微信公众号侧重期刊内容传播,那么它研发的同名APP则构建起开放的文学生态。打开《收获》的APP,读者不仅可以看见其对经典小说的评论与推广,甚至可以免费阅读《香港文学》《北京文学》等其他期刊作品。《收获》APP对跨地域文学资源的整合,推动了文学期刊从“审美圣殿”转向“公共空间”。遗憾的是,除“【无界】阅读”与“天下酒鬼”等少数栏目,其他栏目的内容更新明显滞后。这种传播节奏的明显落差暴露出严肃文学在媒介转型中的阵痛:如何在保持内容深度的同时适应新媒体传播的即时性要求,成为制约其转型效能的关键命题。
此外,网络文学特有的互动机制吸引了严肃文学作家的目光投射。以金宇澄与《繁花》为例,2011年5月10日,金宇澄以“独上阁楼”的笔名,在弄堂网上连载小说《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相较于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城等商业文学网站,弄堂网保留了“邀请码注册”的准入机制,这种类似“文学沙龙”的运营模式为金宇澄的创作提供了特殊的文化场域。弄堂网的用户多为具有“上海情结”的都市中产,在这个具有鲜明地域文化认同的虚拟社群中,使用沪语创作的金宇澄备受关注。当《繁花》经历从网络连载向纸质期刊的媒介迁徙时,金宇澄对小说语言进行了大幅修订,“不能仅让上海人读,20多年做《上海文学》编辑的警觉,一本面向全国的文学杂志,平时处理来稿的方言部分,一样是仔细对待,修改,转化,凡属方言文字,不能有阅读障碍”[19]。如果说弄堂网的地域性赋予《繁花》强烈的方言生命力,那么在文本走向“面向全国”的《收获》时,金宇澄就需要对其进行语言提纯以完成普适化改造。一年后,发表于《收获(长篇专号)》2012年秋冬卷的《繁花》,已经是金宇澄修改了20遍的全新小说了。《繁花》的跨媒介改编说明,文学价值的实现不再局限于媒介本身,而是取决于作者对媒介特性的认识与转化能力。
在新媒体“短文学”中,作家自身成为全新的文艺景观。一方面,业已成名的作家先后开设个人微信公众号,打造数字名片。莫言作为较早拥抱数字媒介的作家代表,其微信公众号自2021年8月发布首篇推文《我为什么叫“莫言”》以来,已经有了长达五年的运营经验。“莫言”公众号的简介为“我想和年轻人聊聊天”,为了实现这一定位,该公众号通过表情包化个人照片、植入采访视频、展示书法与摄影作品等修辞策略,系统性地解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化身份,塑造出具有反差萌感的“邻家大爷”人设。叶祝弟认为:“作家景观化的结果是,如果说过去是读者出于对作品本身的喜爱而顺带喜欢上了作家,那么今天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因为阅读作家本人的作品而顺带喜欢上了作家,还是因为对作家本人的喜爱而顺带喜欢上了他(她)的作品。”[20]这种作家与作品关系的认知倒置说明,当作家成为可被凝视、可被消费的媒介景观,其符号价值开始反超文本的文学价值。
作家景观化转向的深层动因,在于数字媒介对注意力的重新分配,与之形成镜像关系的是素人作家的媒介突围。“素人”是一个描述性称呼,是与专业作家相对应的一种身份指称[21],指向创作主体的非专业化特质。素人作家范雨素曾向互联网致以谢意:“感谢万物互联的互联网,使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家史,每个普通人都能写作,都能留下自己的文字,都能被看见。”[22]范雨素的写作史,实际是素人作家与新媒体的互动史。2014年9月,皮村文学小组在北京创立,张慧瑜、袁凌等人担任志愿者老师,范雨素加入了文学小组,在工作之余开始写作。2017年4月24日,“正午故事”微信公众号发表《我是范雨素》一文,在算法机制的助推下,该文迅速突破百万传播量。4月26日,编辑淡豹发表《关于范雨素的手记》一文,补充了向范雨素约稿的全过程。随后,“人民日报数字传播”公众号发表《全国人民都在问的“范雨素”到底是谁》(2017年4月27日),“凤凰网读书”公众号发表《范雨素“消失”后,我们挖到了更多的内幕》(2017年4月28日)等文章,通过系列报道将个体叙事升级为现象级文化事件。《我是范雨素》之所以能成为爆款文章,其根本原因还是“家政女工”这一弱势身份标签契合了互联网的流量逻辑。范雨素知名度的显著提高也为文学小组吸引了外界关注,他们不满足于新媒体的批量转发,再度回归了文字实践。2019年,皮村文学小组创办的电子刊物《新工人文学》第1期正式发布;2022年,文学小组集体创作的《劳动者的星辰》出版;2023年,范雨素《久别重逢》一书出版;2025年,文学小组的第二本作品集《大口呼吸春天》面世。从文学期刊、个人作品集再到文学选本,文学小组初步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媒介生态循环。值得一提的是范雨素的奇幻小说《久别重逢》,它实现了想象与经验的融合,打破了以往对素人作家只能贴地写作的刻板印象,论证了作家身份转换的全新可能:专业作家可借平民视角重构严肃文学的公共性,素人创作者同样能以生命经验为基点,完成从自我书写到跨界表达的跨越。
钱锺书以“出位之思”概括艺术试图跨越媒介限制的冲动,“每一种艺术,总要用材料或介体(Medium)来表现。介体固有的性质,一方面可资利用,给表现以便宜,而同时也发生障碍,予表现以限止。于是最进步的艺术家总想超过这种限止,不受介体的束缚,能使介体表现它性质所不容许表现的境界”[23]。尽管钱锺书的论析焦点集中于诗歌对绘画、戏剧等艺术媒介的跨界借鉴,但其同样可为文学形态的“出位之思”提供参照。严肃文学、网络文学与新媒体“短文学”正通过媒介互渗实现基因互补:严肃文学在数字链接中主动重组,网络文学吸收严肃文学的叙事深度,新媒体“短文学”孵化出作家的数字名片。新媒介时代固然提供了自由、开放的文学空间,然而这些全新文艺景观的生成,并非全然仰赖新技术,更深植于大众主体性的普遍觉醒。它们集中体现了大众的文艺经验、审美理想与未来愿景:他们试图消解传统文本形态对经典标准的预设,依据个体趣味自由选择文艺参与方式,实现个体创作、阅读与阐释需要的充分释放与自由流动。当大众成为新媒介时代“出位之思”的自觉践行者,“经典”也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范畴,而是获得了与大众文艺实践同步生长的可能。
三、“新大众文艺”的情感引渡
1990年代以来,市民群体的文化需要与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化促使文学场域发生裂变:一端是由学院体制与专业批评共同守护的严肃文学,另一端则是遵循市场逻辑运作的通俗文学。学界对二者关系的认知长期囿于“抵抗”与“收编”的二元框架:一则强调审美分野的本质性,认为严肃文学以“痛感”书写实现“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社会批判功能,而通俗文学则追求“快感”供给,拒绝在“‘严肃—通俗’的序列里接受自己的次等地位和精英的指导批评”[24]。二则侧重文化市场催生的读者导向,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淡化归结为前者对后者的类型征用[25]。上述两种论说均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共生特质:前者将身份认同简化为非此即彼的价值选择,后者则将二者的互动框定于单向度的影响。
然而,新媒介时代的景观融合已充分表明,传统的雅俗对立、精英与民间互斥的话语体系正丧失其阐释效力。实践表明,大众文艺并不排斥与现实人生的深度对话,也未必完全依附类型化叙事。由此观之,“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提出,正是对这一现实困境的理论回应。曾庆香、刘苏仪认为,“新大众文艺”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下,借助互联网及其催生的算法、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媒介技术的驱动,呈现出普通大众广泛参与创作、数据驱动或人机协作、艺术门类互融互通、表现形态融合共生等新特征中的一种或多种的大众文艺”[26]。这一定义揭示了新大众文艺的双重资源,技术赋权消解文学形态的传统边界,人民导向则以情感共鸣建构全新的延展路径。具体而言,新大众文艺的情感共同体表现为创作、观看与批评方式三个维度的同步重构。
在主流话语与民间叙事的情感共振中,创作场域正在经历着开放性重构。通过建立跨越阶层和地域的情感共同体,非虚构写作得以维持十余年的创作活力。自《人民文学》2010年开设“非虚构写作”专栏以来,梁鸿通过《中国在梁庄》等文本,将梁庄转化为留守群体共享的情感场域;阿来在《瞻对》中重勘“铁疙瘩”的历史传奇,建构汉藏文化的情感共同体。然而,专业作家这种“为他人写”的写作立场,容易复现知识分子身份所带来的“中介性”局限[27]。随后,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等作品的涌现,标志着非虚构写作完成了从“精英叙事”到“情感实录”的转变。快递员、矿工、农民工等传统文学中的被书写的“他者”,为非虚构写作提供了多声部叙事。这种全民创作的景象,印证了项静的判断:“非虚构写作在2010年之后被高调地倡导,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即在于重建文学的公共属性和介入性。”[28]当非虚构写作成为大众记录自我生命体验、参与公共对话的载体,其价值早已远超单纯的文体实验,而是一场将个体情感转化为集体记忆的社会学实践。
如果说人民导向让情感共振成为可能,那么技术赋权则通过改变观看方式,强化了大众的情感体验。多媒介的同步呈现催生出全新的文艺形态,游戏叙事为此提供了典型样本。《隐形守护者》与《黑神话:悟空》的破圈传播,分别成为2019年与2024年的重要文化事件。前者通过真人实景拍摄打造极具沉浸感的观看空间,后者在游戏中复现古代寺庙建筑,再辅以声效变化、镜头转换、选择读秒等技术手段,强化玩家的拟真体验。实际上,电子游戏试图激活的情感体验,本身以隐喻的形式存在于玩家的记忆之中。无论是抗战时期地下党员救亡图存的信念,还是《西游记》的反叛精神,这些抽象感知在深度交互体验中全面复苏,转变为可看可感的具身体验。在游戏中,玩家的每次选择会抵达全然不同的故事走向,“这种由读者自由选择故事模块以强化读者参与感的阅读方式,每一次文本块的选择都对应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情节”[29]。当读者身份从被动的观看者转化为文本意义的共建者,屏幕便不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意义生产的动态场域。媒介技术不仅是意义传播的工具,更是情感共同体的显影载体。
再回到批评方式,虚拟身份的建构正深刻改变着文学批评实践。置身于数字媒介之中,大众可以分离“虚拟空间中‘人性化自我’(all-too-human selves)与现实世界‘社会化自我’(socialized selves)”,向外界敞开“由自由主导的精神世界”[30]。去身份化的批评语境催生了新型批评主体,在豆瓣等网络社区,众多“玩家”化身数字时代的“文学评论家”。豆瓣用户“zhy_leon”在体验《隐形守护者》后发表长评:“如果必须有人留在深渊,那我留下好了。如果必须有人承受这一切,我真希望我能一力承担。这样的话,晓曼、小敏、纯子、望舒、君如们就不用过刀尖上的生活,无辜的人就无需日夜担惊受怕。”[31]这段以肖途第一人称展开的精神独白,说明用户在再文本化中成为全新的创作主体。此外,数字媒介提供了便捷的流通网络,让批评实践成为情感共享的关键环节。以《青春》杂志社与茶颜悦色联动的“青春三行诗”征稿为例,参赛者在网络发表诗作后,读者可以通过标签实现精准的内容筛选。读者的点赞、评论与转发,都将离散的个体记忆编织为集体共鸣的情感图谱。有研究者指出,以“玩家”来指称数字时代中的作者与读者更为准确,“游戏也不是指某一种具体的娱乐类型,而是指人们面对文学时体现的主体性、交互性、操控性等,‘玩家’不是指某一款游戏具体的使用者,而是对数字时代文学活动参与者的总体概括”[32]。当“玩家”通过角色扮演实现身份越界,在情感沉浸中展开批判性反思,借数字社区完成意义众筹,文学批评已演变为动态的意义协作实践。
在新媒介时代,技术赋权与人民导向形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关系。作为连接二者的关键中介,情感共同体在其中发挥了隐秘而重要的作用。技术重塑了情感共同体的生成机制,大众可在虚拟空间实现共时在场,让情感本身获得增殖可能。受集体情感影响的大众,可以自觉抵御价值虚无与审美泛化,进而对人民导向作出具体诠释。更进一步,情感共同体为新大众文艺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价值旨归:创作场域的开放与重构消解了专业壁垒,观看过程的具身体验强化了审美感知,批评实践的真实表达构建了平等互动的文艺生态,这些基于情感共同体的文艺实践,共同让“参与式文化”真正落地生根。
结 语
从大众文艺到新大众文艺的演进,实质是大众文艺在媒介革命与文化转型中的自我调适。新大众文艺所面对的,远非文字媒介向数字媒介的简单过渡,而是大众文艺从传统范式向当代形态的转型过程。这要求研究者以“了解之同情”的姿态审视大众文艺的历史形态、把握其内在规律,而媒介正是一个关键的观察角度。正如本雅明所预言的,“艺术作品的可技术复制性改变着大众与艺术的关系”[33]。新媒介时代的关键变革在于,媒介共生不仅催生了新的文艺景观、模糊了雅俗界限,更构建了以情感为纽带、人民为导向的阐释路径。确切地说,景观再生彰显了大众的主体性,情感共同体则推动觉醒的个体寻求共鸣。但这并不意味着个性的消解。通过参与集体对话,大众得以在保持独特性的同时,进一步实现情感共享。由此,“新大众”不再是单向度的受众,也不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概念,它指向所有参与文本生产、传播与再创造的具体个体;“新文艺”亦非雅俗元素的文本拼贴,而是在媒介融通中生成的全新景观;“新大众文艺”虽然容纳不同的形态表达,但在价值层面达成了高度的立场凝聚。值得注意的是,新大众文艺的实践创新持续领先于理论阐释,而这也预示着一个以“参与式文化”为特征、以创造性转化为使命的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1][16]《延河》编辑部《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延河》2024年第7期。
[2] 南帆《“新大众文艺”:从命名到命题》,《文艺报》2025年1月10日,第2版。
[3] 李震《媒介本体化与新大众文艺的潮起》,《文艺报》2025年1月22日,第2版。
[4] 李墨波、刘鹏波、康春华、教鹤然、王泓烨、张昊月《他们是新大众文艺的创造者——东莞素人写作群启示》,《文艺报》2025年4月18日,第2版。
[5][27]欧阳月姣《日常生活与文学诗性之间》,《中国文学批评》2025年第1期。
[6]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文学导报》1931年第1卷第8期。
[7] 郑伯奇《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大众文艺》1930年第2卷第3期。
[8] 鲁迅《文艺的大众化》,《大众文艺》1930年第2卷第3期。
[9]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32-533页。
[10]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周扬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9页。
[11]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1页。
[12]郁达夫《大众文艺释名》,《大众文艺》1928年第1期。
[13]陈晓明《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14]王小峰《只有大众,没有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15]何平《写作者是写作者的身份证姓名》,《北京文艺评论》2024年第1期。
[17]赵勇《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
[18]曾军《“新时代文学”:命名方式、生成语境与发展空间的开创》,《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11期。
[19]金宇澄《〈繁花〉创作谈》,《小说评论》2017年第3期。
[20]叶祝弟《新媒介时代“有故事的人”的炼金术》,《北京文艺评论》2025年第2期。
[21]项静《素人写作:时代文体与经验的公共化》,《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5期。
[22]范雨素《久别重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226页。
[23]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国师季刊》1940年第6期。
[24]邵燕君《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43页。
[25]郭冰茹《当代文学与“中国故事”的话语建构——以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为中心》,《文艺研究》2025年第1期。
[26]曾庆香、刘苏仪《“人民导向”与“技术驱动”:新大众文艺的历史源流、范式重构与发展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
[28]项静《自述与众声:非虚构文学中的素人写作——以范雨素和陈年喜为例》,《学术月刊》2023年第5期。
[29]尹倩《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文学创作与接受研究》,《文艺论坛》2024年第6期。
[30]周铭悦《网络写作是自由写作吗?——技术、商业视域下对网络写作的反思》,《文艺评论》2024年第6期。
[31]豆瓣网,2019年3月4日,https://www.douban.com/review/10021945/?dt_platform=com.douban.activity.wechat_friends&dt_dapp=1。
[32]黎杨全《走向文学的游戏批评范式》,《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2期。
[33][德]本雅明《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经验与贫乏》,王炳钧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