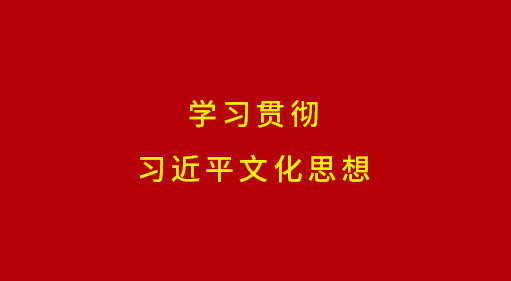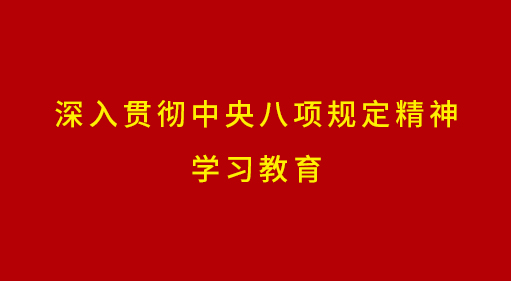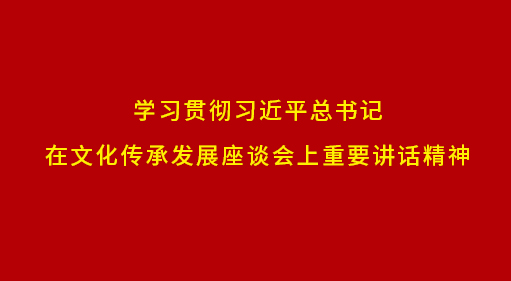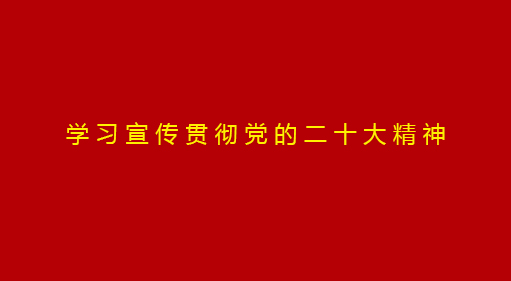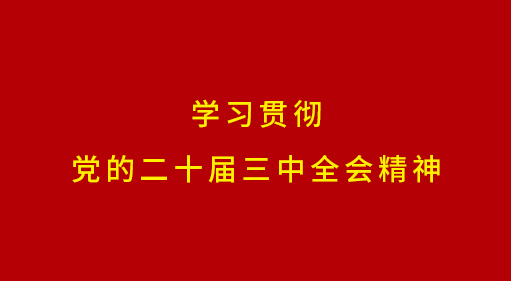“两个结合”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
时间:2025-02-27
李 健 张晓怡
摘 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道路非常曲折,话语体系的建构几经周折。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半个世纪,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高速发展期。学习西方而不废古典,试图构建一种兼容并包的文学批评话语体系。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全面引进、运用苏联的文学批评观念和话语,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文学批评话语建构出现工具化、教条化、过度政治化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转向学习欧美西方,一些批评家甚至将欧美的审美标准奉为圭臬。习近平提出的“两个结合”为改变文学批评的现状提供了契机,既是推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科学态度,也是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科学方法,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两个结合;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西融会;话语体系
文化的繁荣一定伴随着文学的繁荣,文学的繁荣离不开文学批评的推动。中国古代有灿烂的文化,有辉煌的文学。《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与小品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伴随文学发展的是丰富多彩的文学批评。自先秦开始,围绕着《诗经》(先秦称《诗》或《诗三百》)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文学批评观念,诗言志、赋比兴、风雅正变、兴观群怨、温柔敦厚,等等,奠定了古代文学批评繁荣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自觉,涌现出大量的文学批评论著,《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都有卓越的理论发明。尔后,随着文学形式的完善,各体文学的批评兴盛起来,诗话、词话、曲话等独具特色的批评形式成为文学批评的主流,出现了诸如《诗式》《沧浪诗话》《瀛奎律髓》《曲律》《曲品》《四溟诗话》《原诗》《人间词话》等优秀的批评论著,大量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概念、范畴纷纷登场,并以其深刻的理论内涵充实了文学理论与批评话语,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卓然一体,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进入现代以后,随着西方观念的输入,中国文学批评走上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先是中西融会,尝试建立中国批评话语;然后,全面学习苏联,在很大程度上背弃了中国古代的优良传统和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将文学批评工具化、庸俗化;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判话语开始回归文学本身,但有些批评家在拨乱反正的道路上又走得过远,甚至矫枉过正,过于美化欧美,甚至将欧美的审美标准奉为圭臬。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尚未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现代文学批评话语及理论体系,无论概念、范畴还是体系大多借鉴西方,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深刻反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如何发展?我们是否需要属于自己的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怎样才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指出,应继承中国和外国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在这里,答案非常明确,那就是,继承人类优秀的文学遗产,做到“两个结合”。其中的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我们反思与构建现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启蒙与审美批评: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文学批评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纷纭复杂,多线条交织,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条是文化和审美批评,一条是政治批评。这两条线时而独立特行,时而交叉互融,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特征。文化和审美批评的具体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有中西融会的批评,有纯粹借用西方观念的批评,却鲜少纯粹运用或化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批评。这是中国文学批评从古代向现代转型、文学学科独立、文学批评专业化过程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假如后来能对这一现象加以正确的引导,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定会卓然独立,说不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可惜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致使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政治批评干预的结果。综观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这两条线,每一条本身都很复杂,不好笼统而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的文学批评也不好归类。例如梁启超,在他的文学批评中,既有文化的和审美的,也有政治实用的,有时审美的声音很强,有时实用的调门很高。通观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可谓有得有失,成就不小,而教训也多。按照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逻辑发展,我们姑且将19世纪末期以来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历程粗略分为三个阶段,即启蒙与审美批评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政治批评阶段(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批评观念多元融合阶段(80年代初至今)。从这三个阶段的文学批评发展,可以清晰判断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特点。
20世纪50年代以前,文学批评注重的是启蒙与审美批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与西方开始融会。这一阶段,虽然经历了五四反传统风潮,带有救亡图存的强烈使命感,但是,又保持相当的理智。不少文学批评家处于矛盾之中,他们抨击传统,却又深入钻研传统,梁启超、鲁迅、胡适等就如此。很多批评家并没跟风,一方面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另一方面研究西方的文学批评和美学,尝试中西融通,试图构建一种兼容并包、关注时代、启蒙民智、走向现代的文学批评话语系统。王国维、梁启超、鲁迅、朱光潜、宗白华、朱自清、李长之、郭绍虞、陈钟凡、钱锺书等最具代表性。王国维较早引进西方文学理论和美学观念进行文学批评,是融合中西观念最为成功的批评家;陈钟凡和郭绍虞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下分别写出了各自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使得“文学批评”这一概念逐渐流行并深入人心。对此,早在1948年,朱自清在他的《诗言志辨》一书的序中已有初步的评价。他说:“西方文化输入了新的文学意念,加上新文学的创作,小说、词曲、诗文评,才得升了格,跟诗歌和散文平等,都成了正统文学。”“诗文评”“自然是文学批评”,“现在一般似乎都承认了诗文评即文学批评的独立的平等的地位”[2]。显然,朱自清对文学批评独立地位的确立是深感欣慰的。古代的诗文评作为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理应成为现代文学批评研究和参照的对象。
王国维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极其深厚,同时,又深入钻研西方哲学、美学,对叔本华、康德、席勒等人的思想喜爱有加,尤其钟情于西方的悲剧理论。他尝试用西方的悲剧观念评析《红楼梦》。在《红楼梦评论》中,他指出,《红楼梦》属于叔本华所说的“第三种之悲剧”,是“悲剧中之悲剧”[3]。《古雅之在美学之位置》论述古雅的美学特质,运用的是博克和康德的优美和宏壮理论。他指出,古雅不是优美,也不是宏壮,而是超越形式与材质的“第二形式之美”,即“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4]。《人间词话》则以传统的词话形式论述境界(意境)理论,将中国传统的境界与西方的优美和宏壮、理想与写实等联系在一起,赋予境界以新的意义。在王国维的文学批评中,中西概念是交替使用的,中西思想融会贯通。可以说,王国维开启了一个文学批评的新时代。
与王国维同时的梁启超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梁启超对小说批评进行了开拓,倡导“小说界革命”,同时,他还倡导“文界革命”和“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是针对古代僵死的文体的,“以宣扬欧西进步思想为目的,要求用欧西思想来充实文章内容,为维新政治服务”。“‘诗界革命’的根本目的不是抛弃传统诗歌所固有的审美品质,而是意在革除传统诗歌中陈陈相因的思想情感,要求在诗歌之中注入新的思想、新的理想。”[5]文体革新是梁启超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这些批评都与中国文学传统有关,希望革新传统,推动文学的发展。在审美上,梁启超特别推崇“趣味”,而“趣味”正是古人尊崇的审美风尚。可见,梁启超的思想虽然激进,但是,传统文化的情结仍贯穿他的文学批评之中,因此,他的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此后,朱光潜、朱自清、宗白华等都切实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观念与西方观念融会。20世纪30年代,留学欧洲多年、饱受西方文化浸润的朱光潜写作一部《诗论》,论析诗歌理论和批评问题,就将中国古代的诗歌观念与西方的批评观念交织在一起。书中,朱先生讨论了诗的谐隐、境界、意象、情趣、直觉、表现、再现、节奏、声韵、律、顿等问题,很多问题就是站在中西互释或比较的立场来阐发的。这部小书,初步构建了现代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融合中西的态度极为鲜明。在古代文学批评研究方面,朱自清写了四篇长文讨论中国传统的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后来,成就一部经典的文学批评著作《诗言志辨》。书中对中国古代四个核心观念的论析,也是站在中西文学批评观念的立场来进行的,中西融通的意图也极为鲜明。宗白华留学西方多年,具有深厚的西方美学修养,可是,他却将自己研究的重心放在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上。他研究中国古代的意境,游刃于中国古典美学与西方美学的观念之中,以西释中,将意境的“从直观感相的渲染,生命活跃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6]意蕴阐发得淋漓尽致,使得意境无论放在中国还是西方都能够成为一个重要的观念,用以解释文学艺术的诸多现象。
在这一阶段,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学批评家的文学批评也取得了不俗的实绩,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陈说。总之,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文学批评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个良好开端。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一方面注重发掘中国古代文批评的价值,另一方面自觉地引进西方的文学批评,并且能将中西融会在一起,既关注时代,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注重批评的文化维度与审美维度,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启发良多,很多做法是值得今天借鉴的。
二、政治与审美的多元交织:新中国以来的文学批评
新中国以来的文学批评涵盖政治批评和批评观念多元融合两个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两个时间段。具体地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是对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文学批评的承接,也是对它的反叛,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50年代的文学批评的现实关注意识,同时,随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深入,抛弃了政治批评的机械与庸俗,引进西方多元的文学批评观念,同时,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与借鉴上也取得一定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全面引进、运用苏联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批评话语,形成了苏联模式。为了使高等学校快速开设文学概论和文学批评方面的课程,开展文学批评,由高教部出面聘请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来北京大学举办讲习班,传授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7]。北大讲习班结束不久,国家组织编写了2部以苏联理论为核心的高校教材《文学概论》(蔡仪主编)和《文学的基本原理》(以群主编),苏联文学理论在中国流行了30多年,渗透到中国文学批评的肌理。今天看来,苏联的那套理论以他们本土的文学经验为基础,从根本上无法与中国的文学经验相融,与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相融,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其实,就在那套理论在中国大规模传播不久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自身已经开展了对它的清算[8]。苏联标榜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缺乏得自马克思本人著作的学理依据,将马克思主义美学变成哲学或政治的附庸,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建设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9]。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被苏联自己界定为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最终遭到苏联学界的批判。然而,我们接受的恰恰就是这种理论。由于它注重的是文学的意识形态特征,轻视审美,用这套理论开展文学批评,是无法解释文学丰富多彩的美学特质的。这套文学批评理论不仅背离了中国文学的实际,也背离了所有的文学艺术,遭到抛弃是必然的。它虽然标榜的是马克思主义,其骨子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对美的规律的研究,主张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型。
20世纪70年代末至八九十年代,是文学批评观念多元化的阶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们逐渐看清了苏联教条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弊端,开始去除苏联模式,与此同时,大量引进欧美西方的文学理论包括苏俄的语言批评、审美批评和文化批评等观念。这种转变的重大贡献是,将文学从工具化的泥潭中拖出,恢复文学的审美本质,使文学批评回归正途。与世界隔膜了这么多年,突然推开封闭的大门,发现世界变化如此之大,于是,拼命吸纳,多方借鉴,这是本能反应,无可厚非,可是,具体的做法存在瑕疵。那就是,把眼光局限在引介上,只学习外国,不学习古人,一味借鉴,不思创新,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危险。不少学者已经明确意识到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重要性,意识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缺席的荒诞,主张在引进、借鉴西方文学批评观念的同时,应深入开展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将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换,以期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然而,现实的情形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边缘化,而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本身来看,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一些研究者打着尊古的旗号,既不愿意了解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化也知之不深,视中西互释、比较研究为野狐禅;轻视重要理论和核心范畴的研究与阐释,抓到的往往是一个很小的、意义并不深远的问题,总是围绕批评史中的老问题打转;不思考方法的创新,操持的永远是一套陈旧的话语。因为不愿意了解、接受西方文学批评观念,所以无法像王国维、梁启超、朱光潜、朱自清、宗白华等一样以中西融通的视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并将之转化为现代文学批评话语,致使很多有价值的古代文学批评观念和概念无法用于当下。当今,中国文学批评界已经熟悉西方的新批评、接受美学、现象学、语言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形式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将之视为现代文学批评的观念与方法,广泛用于当下 的文学批评,而古代文学批评的概念、观念除了意境、意象、虚实、情景、知人论世等少数之外,绝大多数处于沉寂状态,无法用于当下的文学批评。要彻底改变这种现状,还需要一个消化传统文化、融合欧美西方的过程,需要耐心等待这个过程的完成。有人说,美学、文学理论包括文学批评不应该有中西、你我之别,美学就是美学,文学理论就是文学理论,反对突出中西差异。从学科的建构上看,这种说法似乎在理,但是,其背后隐含的逻辑却不成立。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美学、文学理论包括文学批评都是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基因决定它们必须具备民族特色。大凡统一、包容的学科都不是要取消国家、民族特色,反而更要凸显这种民族特色。因此,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是文化的多元性决定的。
三、第一个结合: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政治方向
全面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可以说,当下仍然没有形成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提出了哪些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创性观念、方法?向世界奉献了哪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创性概念、范畴?产生了哪些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批评家?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真的无法回答。时代需要我们建构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既是推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科学态度,也是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科学方法,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方向。
“两个结合”的第一个结合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落实到当下的文学批评,就是要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开展文学批评,进行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家对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都发表过一些真理性的见解,这些见解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组成部分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必须坚持。虽然很多论述表面上看离文学很远,其实联系很紧密。例如,马克思在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候提出的异化观念,是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认识,而文学是人学,这一理论自然对我们开展文学批评也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如何认识文学对社会现实的描写?如何判定文学对人性表现的水平?都能从异化理论中找到令人信服的依据。再如,马克思提出的“世界文学”观念,应该说是马克思的文学理想。这种观念不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文学,而是要消除文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世界文学”的观念中包含了马克思对文学的民族性的思考。在他看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有自己的传统,都有自己的精华,同时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文学批评应发现这种局限性与片面性,抛弃这些局限性与片面性,便于弘扬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这种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意义深刻。
从中国文学实际出发,就是从中国文学的民族性、艺术性和审美性出发。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文学批评才能抓住根本,彰显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和文学批评的价值。中国文学无论体裁、题材、表现内容、表现方式等都与外国文学存在巨大的差异。中国人的审美虽然在某些方面可能与异国存在相似之处,但绝不可能完全一样。中国文学批评就是要发掘出中国文学的独特性,进而,发掘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的独特性和艺术创造的独特性,以展示中国文学批评的独特性。不加任何辨别,完全把别人的一套观念、方法拿来生搬硬套中国文学批评,显然不合适。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运用苏联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观念建构的批评理论与批评话语,基本上脱离中国实际。受这套理论的左右,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失去了审美性、鲜活性和趣味性,剩下的是庸俗的教条式批评。在这样的批评理论指导下,文学创作只能陷入僵化的泥潭,丧失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丧失审美的多元性。这一教训值得记取。
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艺术创作与审美的标准,文学批评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虽然提倡遵守美的规律,但是,并不意味忽视民族性和多元性。因此,注重实际,实事求是,是构建中国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必须坚持的态度。只有从实际出发,充分吸纳人类优秀的文学批评遗产,才能推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话语体系。这就是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学批评实际结合的要义所在。
四、第二个结合: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建构的指南
“两个结合”的第二个结合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根本。这个结合强调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不意味着“过时”,“优秀传统文化”是具有鲜活的生命力的文化。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许多文化,文化会代代沿袭下去,在传播的过程中,一些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会被淘汰,而一些会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大都是有生命力的,即优秀的。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来看,第二个结合正好直指问题痛点。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第一阶段,即19世纪末至1950年代之前的这一阶段,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话语建构进行了有益尝试。这一时期虽然举着反封建的大旗,但在重视学习西方的同时,也并没有放弃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而是切实将古代的概念、范畴转化为现代文学批评的概念、范畴。这一阶段的很多批评家的做法是较为贴近第二个结合的。王国维就是杰出的代表,他古典文化修养深厚,却虚心学习西方文化,他懂得人类优秀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他曾经这样说:“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10]他运用西方的悲剧观念进行文学批评,同时,不废古典,自觉地进行中西融会。《红楼梦评论》《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人间词话》等论著充分将西方观(概)念与传统观(概)念融会在一起。优美、壮美(宏壮)、悲剧、滑稽、意志、想象、理想、写实、主观、客观、风格、形式等西方文学理论和美学的重要概念,不仅被王国维娴熟地用于对中国文学的批评之中,而且还将之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如意境(境界)、气韵、气象、格调、情景、豪放、沉著、古雅等融会在一起,赋予这些古老的概念以新的理论意涵,意境(境界)、气韵、气象、情景等现今仍活跃于文学批评之中,彰显其理论的活力。如王国维论境界、主观诗人与客观诗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11]诸如此类的论析,在王国维的论著中随处可见。可以说,中国古代的一些文学批评观(概)念之所以能有效参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及其理论建构,王国维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将中西观念置于现代文学批评的语境之中,为中西融通作了良好的铺垫与示范。
与王国维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曾经发表过一些激进看法的梁启超,出于一种自觉的意识,也将西方观(概)念与中国传统观(概)念融会。他写了很多评论文章,如《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屈原研究》《情圣杜甫》《陶渊明文艺及其品格》及《饮冰室诗话》等,都运用中西观念来观照中国古代文学,他用浪漫、想象来评价陶渊明、李白:“我们文学含有浪漫性的自楚辞始。”“楚辞浪漫的精神表现得最显著,莫如《远游》篇。”[12]“浪漫派文学,总是想象力愈丰富愈奇诡便愈见精彩。这一点,盛唐大家李太白,确有他的长处。”[13]且不说这些概念用的是否合适,这种态度却是值得赞许的。同时,象征、超现实以及乌托邦等观(概)念在他的批评中轮番使用,与缘情、温柔敦厚、含蓄蕴藉、境界等中国传统观(概)念融会,即便激进如《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也将理想、写实与境界联系起来。他所说的小说的四种力即熏、浸、刺、提,实是提炼、化用中西观念的产物。此外,活跃于20世纪20至40年代的批评家如朱自清、闻一多、梁宗岱、李长之、朱光潜、宗白华、钱锺书等,都以中西融通的视野开展文学批评,取得不俗的业绩。朱自清、朱光潜、宗白华上文已有介绍。闻一多研究中国古代的神话与诗,充分调动现代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知识,对问题的分析时尚而有深度;梁宗岱论诗,将中国古诗、现代诗与西方诗自由切换,雪莱、魏尔伦、马拉美、莎士比亚与屈原、李白、姜白石等融为一炉,分析他们的诗律、平仄等,新颖,新奇;李长之纵横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欧洲文学之中,讨论文艺的批评精神、文艺史学和文艺科学的区分以及中西文艺理论观念等问题,最早提出文艺美学的概念,倡导“文艺美学者是纯以文艺作对象而加一种体系的研究的学问”[14];钱锺书自觉地将中国传统观念与西方观念比较,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分析应感、通感、诗可以怨等古代观念,都立足于中西诗学,开启了中西观念比较的先河。他们都为第二个结合树立起标杆。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大的缺憾就是远离传统,没有很好地能接续王国维、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等开辟的路径,有效地从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汲取营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不仅形成了严密的话语体系,而且有着极为科学、客观的批评态度,形成了良好的批评风气。这也是我们应该大力弘扬的。例如,曹丕对“建安七子”的批评堪称典范。他提出了“文气”说,从不同的角度(气、文体)评价“七子”的优劣,认为“文章经国之大业”[15],是批评观念的创新。曹丕不是以一个帝王而是以一个读者、旁观者的身份去评价作家作品的,他批评“文人相轻”的风气,对“七子”缺点的批评不留情面。反观当下的文学批评,讲究人情批评、圈子批评,批评流于同质化和平庸化,如此批评,即便与1800年前的曹丕相比,也难望其项背。何以服人?当今的文学批评要想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必须借鉴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学批评观念、范畴,对之进行现代阐释,赋予其新的意涵,同时,也应该学习古代好的批评方法与态度,将之充分运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
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经济的全球化不可避免,而文化依然会保持独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走出一条有特色的道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建成具有民族特色的话语体系,只能落实好“两个结合”。必须认真总结、吸取现代文学批评机械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文学批评的实际之中、没有做好与优秀传统文学批评相结合的教训,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应加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合理而有创造性地引进西方的文学批评观念,进行有机融合,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最终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诗歌的语言艺术原理及其历史生成规律”(编号:18ZDA279);深圳大学卓越重大项目“现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编号:ZYZD2306)阶段性成果]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14期。
[2] 朱自清《诗言志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序第2-3页。
[3]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页。
[4] 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聂振斌选编《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王国维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
[5] 李健《文体 地理 趣味——梁启超与20世纪中国美学》,《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6] 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宗白华全集》(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31页。
[7] 那时,高教部聘请的苏联专家,文学方面的不只毕达可夫一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都有苏联文学专家讲学,只不过,毕达可夫的文艺学课程影响更大一些。
[8] 钱中文在给王忠琪等翻译的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写的中译本前言中这样说:“从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文艺理论发生了激剧的变化。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不断受到清算,各种基本理论问题,如审美的本质,文学的对象和特性,诗学问题,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理论问题,讨论、争论十分激烈。开始我们曾做过一些报导,但是到了6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对苏联文艺理论日益隔膜。”参见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王忠琪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
[9] 汪正龙《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美学问题》,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10]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聂振斌选编《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王国维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
[11]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6页,第27-28页。
[12][13] 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金雅选编《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梁启超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版,第177页,第180页。
[14]李长之《论文艺批评家所需要之学识》,《李长之文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15]曹丕《典论·论文》,郁沅、张明高编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16]关于中国古代文论、外国文论如何参与中国现代文论的构建问题,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有较为详细的讨论。请参阅李健《外国文论如何参与中国现代文论的话语建构》(《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9期)、《中国文论概念的古今之变及其融会策略》(《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11期)。
(作者单位: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