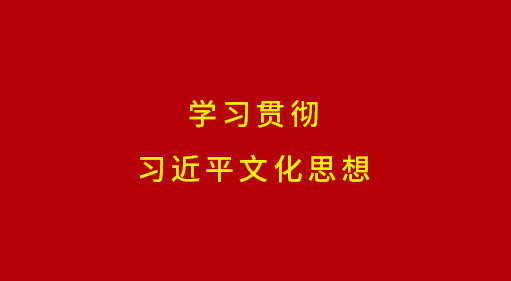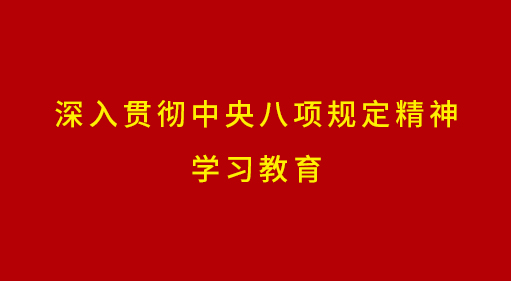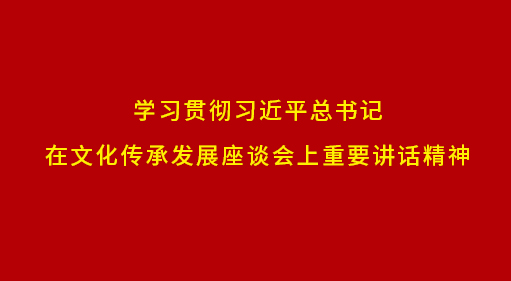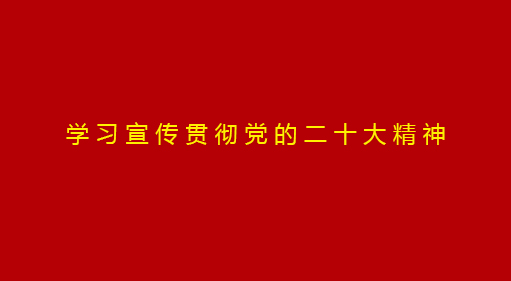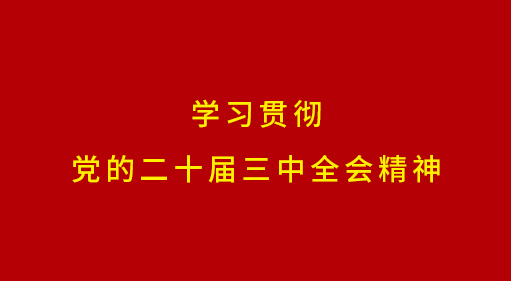重构反叛的场域——对王朔新书《起初·纪年》语言特质的布尔迪厄式考察
时间:2024-12-18
汤凯伟
摘 要:王朔小说创作在新世纪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对王朔在新世纪小说创作的研究数量也极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王朔的语言在新世纪出现了“断裂”并表征为粗糙、呓语、破碎和晦涩。《起初·纪年》面世于王朔创作的特殊时期,其最重要的文学特质是语言依托历史文本完成了对自身语言轨迹的回归,其本质还是利用语言进行戏仿和反讽。王朔语言的回归主要经由化古入今和陌生化两条路径完成,进而使《起初·纪年》在语言上超出了绝大多数的新历史小说的框架,创造出了“顽主风格”的新历史小说。《起初·纪年》的语言背后蕴藏的是王朔暮年之后人生观和历史观的变迁,因此对《起初·纪年》语言的研究就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王朔;《起初·纪年》;历史文本;习性语言
王朔发行的新书《起初》系列的第一本《起初·纪年》是他暌违文坛十五年之后再次推出的一本重量级的新历史小说。《起初·纪年》以海量的历史文本资料为基础,加之王朔本人对历史人物和故事详密的考证,《起初·纪年》以惊人的厚度和深度彰显了王朔希望重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王朔热”的巨大野心。
“起初”系列的另外三本《竹书》《绝地天通》《鱼甜》虽然在内容上与《纪年》不同,但在语言风格上几乎没有变化,因此,本文论述站在“起初”系列总体考察的视角,但以《纪年》为主要考察对象。论述将从布尔迪厄式语言研究的视角对《起初·纪年》这本新历史小说在王朔创作中语言方面的独特贡献作出分析。要厘清《起初·纪年》的独特贡献,首先要回答几个基本问题,其一,《起初·纪年》的语言在王朔创作的语言发展阶段中处于哪个位置?其二,《起初·纪年》的语言与王朔前期创作的语言有哪些相同或相异之处?其三,《起初·纪年》的语言背后蕴藏着王朔对人生、对历史怎样的思考?本文将围绕这几个问题作出阐释。
一、调侃、反讽和呓语的语言轨迹
《纪年》中存在明显的语言轨迹,王朔将自己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调侃和反讽语言重新带入小说创作中。有研究者指出在布尔迪厄的“三位一体”理论中:“习性不仅意味着行动者的位置,还意味着导致他们占据这个位置的轨迹。”[1]在王朔贯穿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除了最早期的三部短篇“伤痕”小说[2]之外,从《空中小姐》(1984)开始,到《看上去很美》(1999)为止,调侃、反讽一直是王朔小说在新世纪之前最显著的语言特征。
反讽是指一套符码两层含义,反讽者经常以扮演小丑的角色来假扮无知者,以此来讽刺那些自认为高明的人物。体现在王朔小说中,就是王朔借痞子式的边缘青年之口,讽刺和亵渎知识分子和伪崇高。诚如王益指出的那样:“小说中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印象,总体上都带有讽刺性或贬义色彩,即使有些看似是对知识分子充满了恭敬,但由于将知识分子的言说放置于小人物们戏谑化或‘痞化’的语境中,于是‘知识分子’也就自然成了小人物们调侃式生活场域中的‘助推剂’。”[3]《顽主》《一点儿正经没有》《你不是一个俗人》将宝康(作家)、赵尧舜(德育教授)、古德拜(老作家)、吴汉雄(学者)、关科长等知识分子刻画得十分丑陋,王朔总是先用一种崇拜的口吻捧高他们,然后再利用这些人物的伪善的丑恶面孔将他们打到谷底,原形毕露。
新世纪开启之后,王朔创作的散文评论引来了巨大的争议,并且发表《我看金庸》(《中国青年报》1999年11月1日)、《我看老舍》(《作家》2000年第2期)、《我看鲁迅》(《收获》2000年第2期)、《我看王朔》(《北京青年报》2000年1月11日),以及《三联生活周刊》从第4期到第15期发表的“狗眼看世界”系列12篇批判性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王朔不乏对老一辈作家的批评之语,像“他(指老舍)的小说也是瑕瑜互见,良莠不齐。我觉得写得不好的首推《二马》和《四世同堂》”[4]。还有“初读金庸是一次很糟糕的体验,开始怀疑起那些原本觉得挺高挺有卤的朋友的眼光,这要是好东西,只能说他们睁眼瞎了”[5]。并且认为鲁迅“各界人士对他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6]。王朔敢对著名作家大放厥词的行为引来了无数酷评,仿佛是文坛中正道与邪道的较量,“狗眼看世界”更是让王朔把社会现象都批判了一把,他对张艺谋、白岩松、“知道分子”、影视剧“游戏规则”的揭露和讽刺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在这段时期内,王朔一改以往反讽式的暗藏机锋的语言方式,对著名作家、社会名人、文化现象作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王朔的语言风格到此就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这种断裂在王朔新世纪之后的几部作品中,就表现为作品在语言上的粗糙、呓语、破碎和晦涩。如新世纪之后王朔曾对佛禅的“觉悟”十分感兴趣,因此他试着用北京话解释佛教经典,在《我的千岁寒——取材于〈六祖坛经〉》的开头,王朔将“时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名璩,与官僚入山”[7]解释为:
时——觉悟者释迦族的明珠湮灭物质形式回归能量圈两个五百公转儿后,第三个五百公转儿内。
大——欧亚陆架中央隆起雪山发源之水越撇越长撇出一江一河流入太平洋,流域地区是唐朝——女士主政时代。
师——我该挎弓没挎弓挎着麻绳和柴刀,一顶斗笠,一手提拳一手下垂,走在亚洲板块遭太平洋板块推搡起这一层由南滚向北的皱褶肌纹中。
至——东经24度,北纬113度大约莫之间,有一土堆叫南华,鼓包上有一叫宝林的勾腿盘坐和尚食堂。我去蹭朋友饭,饭已忘,朋友名已忘,都不重要了……[8]
从上文所引的这一段原文可以看到,王朔对《六祖坛经》的释义晦涩难懂,并且其间掺杂了许多无关联系、意义含混的呓语,令读者无法理解。而且不只对《六祖坛经》的释义是如此,王朔还对《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西藏度亡经》《金刚经》都作出了呓语式的释义,这些令人难解的释义和王朔本人对佛法的狂禅式理解是相互吻合的,在王朔看来“心外无佛”,佛经也就可以随着每个人内心的想法有个人化的理解。
如果说对佛经晦涩的释义还能以个人觉悟的理由来解释的话,那么王朔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两部小说《骇思想》和《死后的日子》就更能代表王朔在语言上的断裂了。《骇思想》大体记录的是王朔那段在北京待腻之后去美国的时间里心理活动,全文由王朔的心理描写组成,例如:
实在不像的就不说了,压根没摸着门儿的就算了,天生的戏子就算了。允许有一些塌儿哄,允许有一些蒙事人民很闲在。允许有一些出身局限性格差池必须仗着人点。允许有时代蹄子印烙铁印。允许青春过不去就觉得小时候好就不长大年夜饭忘不了。允许念书念的就是这碗饭日后还真把这碗当饭了,有年头,有感情——否定他就是否定自己;有饭票,支持您登堂,支持您入室,荣耀了您,膝下葱茏,心里也早悄然认了干爹,还是见滴水思涌泉,您叫涌,他就叫泉,你们俩是绝配,是二踢脚,一响在您手上,一响在他身上,是条汉子,允许。[9]
一个想法连接着一个想法,一个观点连接着一个观点,这些想法观点互相之间没有任何逻辑顺序,一念还未灭一念又起,语言之间排列杂乱无章,没有任何思维停歇的空隙,就如人在崩溃之时万念俱发。《死后的日子》则是王朔将自己死后的妄想付诸文字的作品,与《骇思想》破碎、杂乱的语言风格类似。
王朔在新世纪作品语言的粗糙、呓语、破碎和晦涩等特点,以至于对《我的千岁寒》(2007)、《致女儿书》(2007)、《新狂人日记》(2007)、《和我们的女儿谈话》(2008)这四部作品,极少有研究者能够将之纳入对王朔语言的整体探究之中。《起初·纪年》正是在王朔创作语言呈现破碎状态的时候面世的,从《起初·纪年》在语言上的严谨和历史感来看,《起初·纪年》是王朔走出21世纪之初“认知障碍”和“精神分裂”之后,依托历史文本,有意识地重新组织自己语言的结果。
《起初·纪年》面世于王朔创作的特殊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特质是其语言依托历史文本完成了对自身新世纪之前语言的回归。《起初·纪年》是王朔继《和我们的女儿谈话》(2008)之后,向读者推出的四卷本历史小说《起初》系列的第四本,之所以先出版第四本,是因为这卷“文字最顺,阅读体验最好”,亦是可以让王朔自己“安心调整主要是删改各前卷,满意一本推出一本,不负读者”[10]。由此可见,十五年过后,王朔的心态不再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急于“拿小说做敲门砖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的青年作家,这从《起初·纪年》所选择史料参考的跨度就可见一斑,《起初·纪年》据王朔自己所说参考了《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所载汉武旧事,“有些例行封赏宴飨通鉴不如汉书详备则由汉书补入,也是为了显得文体庄重”[11],但阅读完整本书之后,发现其实参考的资料远远超出这些,尤其是对张骞羁留匈奴十年中西域各国的掌故进行过详细的考证,如对匈奴史诗《康泽曼刚巴尔》《阔尔奥格立》《阿勒帕米西》等如数家珍,对张骞出使西域历经的巴克特里亚文明、塞琉古王朝、米底王国、阿赫门王朝等古文明史实一一列举,非考证西方古文明史不可得,不仅如此,《起初·纪年》超五十万字的篇幅也是王朔所有长篇小说中最长的[12]。《起初·纪年》是王朔下了很大心血的一本书,这尤其体现在《起初·纪年》的语言上,《起初·纪年》是王朔利用调侃的反讽的语言来叙述历史,既使历史变得妙趣横生,又让王朔的小说语言在词语、句法上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二、《起初·纪年》回归调侃和反讽语言的两条路径:化古入今与陌生化
以历史文本为基础创作的小说在中国十分常见,也十分受读者的欢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坛涌现了一大批以历史小说创作为主的作家和作品,如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唐浩明的《曾国藩》《杨度》、凌力的“百年辉煌三部曲”(《少年天子》《倾国倾城》《暮鼓晨钟》)、徐兴业的《金瓯缺》、高阳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熊召政的《张居正》《大金王朝》、孙皓晖的《大秦帝国》,等等,历史小说因其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而深受大众读者喜爱。但以往的历史小说常常以严肃的态度结构故事,表现在语言上就是追求“拟古化语言”[13],而《起初·纪年》在同样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改变叙述故事的语言,因此在语言上的虚构是《起初·纪年》最大的特色。
海登·怀特在《话语的转义》中指出:“人们一直不愿意把历史叙事视为其显然之所以是:语言的虚构;其内容被发明的成分不亚于被发现的成分;其形式与其说与科学的形式相似,不如说与文学的形式相似。”[14]海登·怀特在这里指出的是历史其实也属于语言上的虚构文本,因历史文本也就常常被文学家所利用,将历史的语言替换成文学的语言,并且在历史的缝隙中添加自己的想象来敷衍成篇,古今中外佳作迭出。在西方,如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约瑟夫·海勒的《上帝知道》等,在中国,则以王小波的《红线盗盒》和《红拂夜奔》为代表。
总的来说,《起初·纪年》对语言的回归有两条主要路径:其一,化古为今,由庄入谐。如对古词“警跸”的解释:
(马迁按:时,长安在长乐未央两宫门外、北阙甲第胡同口、甲一号院、北军总院几个重要机关路口都建立了根据灯笼指示通行制度,红灯笼停,绿灯笼行,由各单位看门大爷执行,平时挂红灯笼禁行,上銮驾一路绿灯笼,当时不叫交通秩序,叫警跸)[15]
改编司马相如《喻巴蜀檄》《西征论》等赋成现代版,如“蛮夷一向擅自做主一副找打的样子”,“伸着脖子,踮着脚,张嘴哼唧争先归顺我汉”[16],“如果不拿他们当外人,他们就会蹬鼻子上脸毫无礼义廉耻侵扰我国边境”[17]等,将言辞壮丽的古文化为浅俗诙谐的现代语言。
除此之外,王朔对古文的化用还包括对传说中存在的书籍的创造,《三坟》《五典》传说是伏羲、黄帝、神农、少昊、颛顼等人留下的文献,世上不存,王朔却自己创造了三条《三坟》名言:
《三坟》有言:恩养动物的人有福了,因为我必不使她永堕黑暗。
《三坟》还有言:凡睁开的眼,我必不使她不再合上。你已然醒了,再也装不成睡。[18]
《三坟》说:总要好也经过,坏也经过,才不再来。[19]
王朔创造的这三条《三坟》名言在文中都用在哄后宫的后妃身上,或许王朔是刻意将《三坟》化用为哄女人的经典,其中谐谑反讽的意味十分强烈。
其二,将语言再次陌生化。《起初·纪年》虽然通篇是用京味方言叙事的,但其中使用的京味方言与王朔之前使用的以“北京现代流行语”[20]为主的京味方言有了很大区别。在王朔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的小说中,对政治话语的戏拟式运用和北京青年流行黑话的滥用是其主要特征,《顽主》《一点正经没有》《动物凶猛》《千万别拿我当人》等篇是这种京味方言的代表,而《起初·纪年》则刻意突破了这种已被广大读者熟悉的王朔语言。其方式主要有三:
首先,扩大词汇量和因音改词是主要手段,北京方言很多有音无字,王朔就遵循以象声词代和从俗的原则来创造新词,除了王朔在自序中提到的将“那什么”改为“内什么”,“接壁儿”和“界别儿”并用,老实巴交、烂七八糟改为“老实芭蕉”“烂漆疤糟”外,还有将“怎么着”改作“怎么遮”,“八卦”改作“扒褂”,“厕所”写作“次所”,“缘分”写作“猿粪”,“是吗”写作“湿妈”,“尾巴”写作“以巴”,“幽默”写作“油墨”,并且在大段的北京方言后,用陕西方言或山东方言“破”一下语境,其实也是增加读者的新鲜感,像书中的王太后就说陕西话,兒宽说山东话。
其次,据《起初·纪年》的编辑孙腾说,王朔在《起初·纪年》中无论如何都不想出现字母,因此在《起初·纪年》里出现了许多翻译词(如土耳其语、乌尔都语等)。如文中匈奴话音译成“赤马虎”“特马者”“音色拉”“因赛姆地”“阿努努”“柯蓝微蓝”“克斯卡逮甚”,古夏语的“阴麻针”等等。
最后,《起初·纪年》中出现了王朔以往小说中很少出现的各类军事指挥用语。王朔在《自序》中承认:“另一个不好意思的原因是我幼时其实是个军迷或叫武人崇拜者……初衷有相当成分意图借汉武朝军事活动把本人军迷时代攒下来的小爱好、小见识发挥一下,过过瘾。”[21]《起初·纪年》中出现的军事指挥用语涉及面非常广,王朔将汉匈之间的战争按“武装力量当前实力、战争动员体系、兵员构成、武器装备、指挥层级、惯用战术和补给模式”[22]次第展开,事涉情报战、道路修缮、武器装备、马匹储备等等,事无巨细,难以穷举,读者犹如坐在作战室内,面前就是巨大的沙盘,十分过瘾。
总而言之,语言上的化古为今、由庄入谐和陌生化让《起初·纪年》在语言上超越了绝大多数的历史小说,王朔的《起初·纪年》并不是要书写伪历史,而是要用真语言书写真文学。作家止庵在对《起初·纪年》进行推介时,在微博上写道:“我读《起初》,诚心诚意佩服作者巨大的想象力,完满的表现力,惊人的运用语言的能力,高超的结构与塑造人物的能力。过去我们常说,王朔难以被同代及后辈的作家所超越,现在王朔超越了他自己。这似乎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却也在情理之中——只有他肯下这么大功夫,只有他能有如此收获。”[23]止庵对《起初·纪年》的赞美并未言过其实,但是,《起初·纪年》的巨大、完满、高超都是建立在王朔“惊人的运用语言的能力”之上的,王朔在《起初·纪年》中对京味语言的再发现是《起初·纪年》乃至《起初》整个系列最重要的收获,或许因此语言上的贡献,王朔及其创作能够在当代文学史中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三、重新构建的反叛的场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王朔是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存在的。余华说他一直在想王朔究竟是怎样与时代如此紧密的,这是其他作家无法达到的;戴锦华说王朔用自己的那种调侃帮助我们走过那个迷惘的年代,但背后其实是很深的痛;马未都说王朔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影响过一代人。如果说20世纪对王朔及其作品的评价还相对驳杂的话,《起初·纪年》则完全揭示了王朔为何能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偶像的原因,以及王朔的作品为何在他沉寂十五年之后一经发售,便形成了洛阳纸贵的局面。
虽然王朔在新世纪之后一段时间曾经在文学创作中迷失过,但时至今日,王朔已经重新接续上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的反叛精神,如果说王朔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创作是霓虹歌舞厅,那么新世纪之后的创作就是一片废墟。“起初”系列则表现出了王朔重建歌舞厅的文学倾向,他将世界、历史再次构建为文学反讽的对象,可以说王朔经历了一个类似布尔迪厄自我理解的过程:“理解,就是理解一个场,一个人与这个场一起并通过反对这个场而形成。”[24]王朔以知识分子反叛者的形象进入文学核心场,又因为反叛而被文学核心场发配到文坛边缘而失去发声的权利,当王朔再次回到文坛的时候,他又是以反叛历史的姿态回归的,因此,“起初”系列代表了王朔对自身和当代文学场关系的重新认识,即王朔认为目前的当代文学创作缺少调侃反讽语言风格的作品,缺乏反叛精神。
必然还是王朔的语言。陈思和曾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有先见地指出过“历史的反讽是王朔小说的基本心态”[25],他指的是王朔小说对政治话语和文学教育功能在上个时间段独尊地位的反讽,确实80年代王朔创作的小说如《橡皮人》(1986年)、《顽主》(1987年)中大量地对政治话语和知识分子进行了无情的反讽,当时王朔运用的武器就是他犀利的语言。
《起初·纪年》重新找回了这种反叛的态度。王朔之所以要将《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正史用自己的特有的语言重新改写,一方面是想用自己的想象将汉武故事串联起来,添入矛盾冲突、人物性格,以符合小说的体例;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起初·纪年》是王朔将批判性的目光从身边的生活投向了更为久远的历史,将抽象的概念化的人物、事件化为有血有肉的、可感可触人物和事件,来解构严肃庄重的历史,这一切都是通过反讽戏谑的语言完成的。
在史书记载中,汉武一朝穷兵黩武,自建元始到后元终,无一个年号不在打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十四》中评价汉武帝是“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26]。后世的文学影视作品也常常将汉武帝塑造成一个好战武断、晚年多疑、滥杀无辜的帝王,在《起初·纪年》里王朔却将汉武帝及群臣塑造成一个类似《顽主》里于观、马青、杨重似的哥们关系,王恢、灌夫、唐蒙、韩安国不似臣子更像和汉武帝是战友关系,汉武帝经常与群臣侃来侃去,一起撸串吃烧烤,有事情一起商量着来,为人臣子的,动不动向皇帝呲一句,完全不怕国法威严。
王朔要反叛的正是所谓历史学家的正史观念,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将历史限制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任何超出界限的证据都会被认为是伪历史,正如海登·怀特指出的:“历史不仅是过去以过时的制度、观念和价值的形式强加给现在的一种沉重负担,而且也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它赋予这些过时的形式以华而不实的权威。”[27]《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看待历史的方式是有其时代局限的,因为宋代儒学盛行,所以《资治通鉴·第十七》汉武开篇是以董仲舒的《举贤良策》为主的,但王朔在通读了各种史料时候,发现汉武时期尊儒是有形无实的,因此《起初·纪年》中就对儒学保持了一种客观的态度,也并没有占很多的篇幅。其实王朔就是在挑战历史的权威,无论是他在书中用现代语解释古词、创造《三坟》名言,还是将司马相如的赋变成浅俗的大白话,都是在表明王朔对正史的态度——反叛。
反叛的态度并不仅仅指向正史文本,王朔将自己的语言再次陌生化也是对自己的一次反叛。众所周知,王朔的语言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受到很多批评家的关注,有些批评家将王朔作为京味文学的第三代掌门人,是老舍的直接继承者[28],有些批评家专研“王朔小说的反讽艺术”[29],还有的批评家在语言的层面上将王朔视为“历史小说家”,因为王朔唤醒了中国人的“语言无意识”[30]。王朔已经出版的小说也被读者们所热捧,一般来说,一个作家一旦适应了一种语言,想在语言上有所突破是非常难的,但王朔能够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与他自身的叛逆精神有很大关系。对王朔来说,沉浸在温柔乡或是旧有的辉煌里是不令人满足的,并且王朔在新世纪的创作并不被人们所看好,有人预言王朔已经江郎才尽了,令人钦佩的是,王朔并不认可这一点,他觉得自己这种才也许尽了,但另一种才或许就来了,《起初·纪年》就是王朔另一种才完美的证明。
可惜的是,《起初·纪年》虽然是王朔对历史和自我的一次反叛,但这反叛并不彻底。这既表现在《起初·纪年》对《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等历史文本在事件编排和史实上的不违背,也表现在文中语言上对正史原文本语词的过度借用上。纵观《起初·纪年》的章节编排,不出《资治通鉴》的编年体例,小说这样编排就已经天然决定了它在叙事技巧上的缺陷,因此《起初·编年》的叙事是比较混乱的,《资治通鉴》的客观视角必然限制王朔以第一视角写作小说,《起初·纪年》里各节之间叙事视角不统一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小说的后半部分,客观第三人称视角占据了大部分的叙述,后半部分的叙事语调明显沉闷。
全书的情节设计比较露骨,与史书相左的地方不多,人物的命运起伏与史书相一致,令人眼前一亮的情节很少。并且,为了保证小说中语言的历史感,《起初·纪年》中对史料原文本的语词进行了大量的借用,造成了王朔自己的语言和司马迁、班固等人的语言在小说中互相冲突,总体来说,小说前半部分语言上的冲突比较少,将古文化用为今文处理得比较顺畅,而小说的后半部分能明显感觉出王朔的语言难以化入史料中,在语言上还有未完满之处。
《起初·纪年》时隔十五年再一次向读者们表明,在当代作家中,王朔在语言上的造诣依旧独领风骚,也再一次证明王朔不仅是一个只会对自己生活进行非虚构创作的作家,还是一个对完全虚构生活同样有极强创作能力的作家。《起初·纪年》是对《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的汉武帝年间人物、事件的改编,使用的是王朔特有的语言,王朔通过化古为今、陌生化等语言形式,表现出了对历史的反叛态度,消解了历史的权威带给现代人的沉重感,能够让读者在阅读时感到有趣和轻松。当代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屈指可数,唯有王小波和王朔而已,王小波的青铜时代已经远去,幸好我们还有王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期以来作家‘文学谈’研究”(项目编号:23BZW154)阶段性成果]
[1]刘晖《布尔迪厄的文艺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45页。
[2]指《等待》(1978)、《海鸥的故事》(1982)以及《长长的鱼线》(1984年)这三部短篇小说。
[3]王益《卸下面具——王朔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心态研究》,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4]王朔《无知者无畏》,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5]王朔《我看金庸》,《王朔研究资料》,葛红兵、朱立冬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6]王朔《我看鲁迅》,《收获》2000年第2期。
[7]《六祖坛经》,徐文明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8]王朔《我的千岁寒》,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9]王朔《新狂人日记》,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10][11][15][16][17][18][19][21][22]王朔《起初·纪年》,北京:新星出版社,2022年版,第1页,第32页、第219页、第416页、第238页、第293页、第2页、第11页。
[12]之前最长的为《我是你爸爸》,19万字出头。
[13]汤哲声《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页。
[14][27][美]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第43页。
[20]参见周一民《北京现代流行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北京现代流行语》中收录了很多王朔小说中出现的北京流行语。
[23]止庵《推荐一本书》,《新浪微博》2022年8月12日,https://m.weibo.cn/1229587265/4801541460984832.
[24][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自我分析纲要》,刘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25]陈思和《黑色的颓废——读王朔小说的札记》,《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5期。
[26][宋]司马光《卷第二十二 汉纪十四》《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61页。
[28]具体论文参见王一川《与影视共舞的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文学——兼论京味文学第四波》,《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王一川《泛媒介场中的京味文学第三代》,《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王一川《媒介变化与京味文学的终结》,《求是学刊》2005年第2期;王一川《京味文学:绝响中换味》,《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王一川《京味文学的含义、要素和特征》,《当代文坛》2006年第2期等文章。
[29]杨剑龙《论王朔小说的反讽艺术》,《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
[30]张清华、程大志《由语言通向历史——论作为“历史小说家”的王朔》,《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作者单位: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