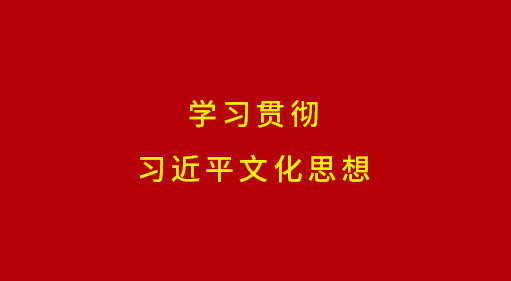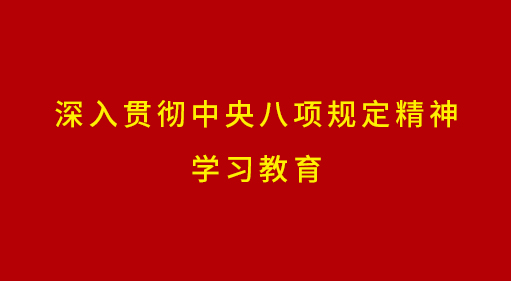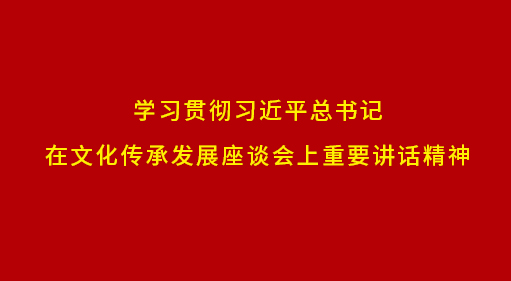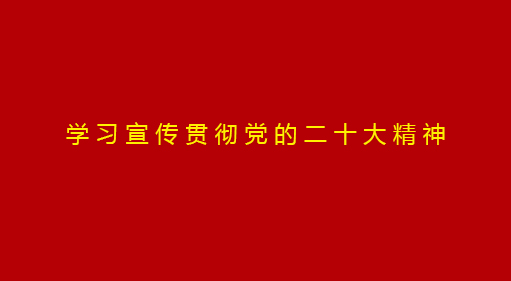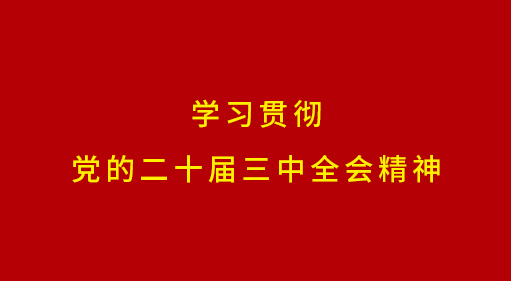从“致用”到“立知” ——20世纪早期现代中国文学立科的根基及其当代启示
时间:2024-07-08
宋 刚
摘 要:20世纪早期,现代中国文学立科经历了三个重要节点。首先是晚清政府拟定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其本着“经世致用”的理念设立文学科,将文学视为通往经学的门径与手段,试图保持其“文字之学”与“词章之学”的传统意涵与意识形态属性。其次是王国维引入西学,强调学术分化的科学性与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将文学学科建基于审美非功利性的学理之上。最后,朱希祖的《文学论》标志着文学研究以系统化、理论化与知识化的方式,完成了由传统“致用”向现代“立知”的学术转变。这个过程表明,支撑文学立科的基础是由“知”与“用”两部分构成的,二者不可偏废。在介入与静观之间,既离不开知识化的学理分析,也应重视古代“作文”传统的当代转换。
关键词:文学立科;京师大学堂章程;致用;立知
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自晚清京师大学堂设置“文学科”算起,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了。整体而言,这既是中西文化碰撞与会通的产物,也是现代学术分化的必然结果。20世纪早期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立科的“发生”阶段,其对整个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美学思想、知识分类体系以及现代高等教育模式的输入;而这一演变给中国文学知识带来的影响,最突出的就是纯文学意识的产生和现代文学学科的确立”[1]。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似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线索与依据。更为重要的是,文学立科问题还直接与文学教育的理念与实践相关。质言之,文学学科的建立不仅是要追求有关文学的确定性知识,同时更要培养学生通过“作文”而介入日常生活的能力。
一、“经世致用”与文学立科
华勒斯坦说:“19世纪思想史的首要目标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2]由于中西之间现代化进程的时间差,中国在20世纪初才真正开始这个过程。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劲势头,晚清政府在文化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莫过于引入西方现代教育制度,旨在通过现代教育培养兼通中西的人才,以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具体到文学学科上,通过其拟定的三个京师大学堂章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发展过程与努力方向。
京师大学堂拟定的章程前后共有三个,分别是《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1898)、《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和《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4)。主要是参照英美日三国的学科建制来制定的。《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合“维新变法”,由梁启超起草。章程共七章,其中涉及文学的是第二章“学堂功课例”,主要参照日本与西方学科分类,分为“溥通学”和“专门学”两类。前者近似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必修基础课程,所有学生都要学三年,完成十门功课。主要包括:经学第一、理学第二、中外掌故第三、朱子学第四、逐级算学第五、初级格致学第六、初级政治学第七、初级地理学第八、文学第九、体操学第十。这期间还需要学习一门外语,之后就可以进入“专门学”进修一门或两门,其中包括高等数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以及农学、矿学、工程学等十种专门学。经学第一,为众科之首,自然可以看出经学在学科设置中的统帅地位。文学具体指的是什么,章程中并没有交代。但根据梁启超《万木草堂小学学记》中对“词章不能谓之学”的论述来看,这里的“文学”主要还是指传统的“文字之学”,其学习主要目的在于实用,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但不是创作“骈俪之章”和“歌曲之作”,以免沉溺丧志。[3]尽管“文学第九”仅排在“体操学第十”之前,也没有进入“专门学”,但这并不能说明文学科地位不高。因为将“文学”与中国传统学问经学、子学放在一部分里,显然强调的是文学科在育人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说明文学立科在“致用”,而不在于探求关于文学的某方面知识或技能。
第二个是《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由时任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在官学大臣张百熙的支持下,通过实地考察日本的教育政策后,重新拟定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后经慈禧太后接纳,因此称作“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颁布的时间是农历壬寅年,所以又叫“壬寅学制”。在学科门类上,《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共分为七科: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文学科”下面又分为七目: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由此可见,“文学科”,近似于今天的文学院,文学所指乃是词章之学。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章程并没有付诸实施。
第三个章程《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对文学立科的影响最大。1903年清政府命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厘定学堂章程,1904年初颁布施行,因为是农历癸卯年,所以又叫“癸卯学制”。该章程把大学堂分为八科:经学科大学、政法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医科大学、格致科大学、农科大学、工科大学和商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分为九门:中国史学门、王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文学门。中国文学门又分主课与补助课。主课七科包括: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九科包括:四库集部提要、汉书艺文志补注隋书经籍志考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种记事本末、世界史、西国文学史、中国历代法制考、外国科学史、外国语文。此外还有“随意科目”,第一年是心理学、辨学、交涉学,第二年是西国法制史、公益学、教育学等,第三年是拉丁语和希腊语。章程还配有“中国文学研究法略解”和“各科学书讲习法略解”提供具体教学指导和授课内容说明。“中国文学研究法略解”中指出了研究文学的要义,涉及文字、音韵、训诂、文章修辞、写作、文体文法,以及文学与国家、地理、考古、外交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等论述,有点近似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学概论和文学史的杂糅。“各科学书讲习法略解”中指出“历代文章流别,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4]。当时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的林传甲就效仿日本笹川种朗《中国文学史》而编写了“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就是后来的《中国文学史》。但是内容上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按照“中国文学研究法略解”来展开写作的。“历代名家论文要言”有点近似于文学批评史。总之“中国文学门”所涉及的内容已经很接近于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框架了。只不过还是杂糅在一起,没有自觉地分化开来。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文学研究法略解”和“各科学书讲习法略解”等内容中间,反复强调了作文的方法以及词章为文的实用性。“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修辞立诚、词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记事、记行、记地、记山水、记草木、记器物、记礼仪文体、表情文体、目录文体、图说文体、专门艺术文体皆文章家所需要。”[5]也就是说作为词章的文学,在应用层面上,要学会多种文体写作,其中涉及艺术与情感方面内容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而且文章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就足够了,不用太过华丽。“各科学书讲习法略解”中也指出:“凡习文学专业者,除研究讲读外,须时常练习自作,教员斟酌行之,犹工医之实习也,但不宜太数。愿习散骈体可听其便。”[6]“博学而知文章源流者,必能工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7]这里所反复强调的是写作实践的重要性,但是对于诗赋方面则没有过多要求。
对于《奏定京师大学堂》文学立科的根据,我们可以从与之一起颁布的《奏定学务纲要》中获得清楚的说明。
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古文所以阐理纪事,述德达情,最为可贵。骈文则遇国家典礼制诰,需用之处甚多,亦不可废。古今体诗辞赋,所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中国乐学久微,借此亦可稍存古人乐教遗意。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文学既废,则经籍无人能读矣。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此即保存国粹之一大端。假使学堂中人全不能操笔为文,则将来入官以后,所有奏议、公牍、书札、记事,将令何人为之乎?行文既不能通畅,焉能畀以要职重任乎……今拟除大学堂设有文学专科,听好此者研究外,至各学堂中国文学一科,则明定日课时刻,并不妨碍他项科学;兼令诵读有益德性风化之古诗歌,以代外国学堂之唱歌音乐。各省学堂均不得抛荒此事。凡教员科学讲义,学生科学问答,于文辞之间不得涉于鄙俚粗率。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但取理明词达而止,以能多引经史为贵,不以雕琢藻丽为工,篇幅亦不取繁冗……高等学堂以上于中国文辞,渐求敷畅,然仍以清真雅正为宗,不可过求其古,尤不可徒尚浮华。[8]
“不废中国文辞”一是为了训练士人写文章的技能,使其能够应对日常中对奏议、公牍、书札等现实需要。二是在于其文化属性或者说是意识形态性,即文学作为进入经史之学的一个门径与手段,为士人提供安身立命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样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涌入时,才能够保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所以,面对时势,不仅要文以载道,“更兼有文以载政之用”[9]。《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整体上无疑是经世致用思想的产物,或者说是在西方文化刺激下的某种制度上的回应。文学科目的设立,虽然不离实用,但是总算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而存在了。当然,这门独立的学问,并没有真正地关注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文学的观念也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但是这并不影响文学以“致用”的目的而独立。并且,以今天的视角来反观这个学科设置,这似乎也是一个更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课程体系与学科框架。其拟定过程如张之洞所说:“数月以来,臣等互相讨论,虚衷商榷;并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其于中国不相宜者缺之,科目、名稠之不可解者改之,其有过涉繁重者减之。”[10]由此可见,这正是“中体西用”在文学学科上的展开与应用。这也说明了,学科的设立并不仅仅是学术分化问题,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与文化发展的路线问题。
二、“无用之用”与文学“立知”
《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颁布后,遭到了王国维的批评。1906年,王国维发表了《〈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从学理出发对章程中没有设立哲学以及将经学与文学分开表达了不满。他在学科课程设置中引入了哲学与美学课程,强调西方哲学系统性、理论性对于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力图以西方美学为文学研究确立原理,将文学学科建基于审美非功利性的学理之上。
第一,引进西方哲学的必要性。王国维对章程的最大不满,莫过于其没有设立哲学。其实早在1903年,他在《哲学辨惑》中就已经针对当时士大夫对哲学的误解给予了澄清。一方面,王国维认为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所以学科设置中没有哲学是不妥的。他指出,学科设置虽然在经学科大学中附设了理学,但其范围仅限于宋以后的学说,且其宗旨在于“贵实践而忌空谈”,所以只包括了中国哲学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王国维指出了研究西方哲学的必要性。其一,中国现实之需要。这一点主要是指教育学上的需要。当时晚清政府试图通过教育改革、培养通才来挽救危亡,所以造成一种全国上下谈教育的风气。但是,人人谈教育却无人谈哲学,王国维认为这是一大错误。因为在他看来,教育学离不开哲学,其不过是心理学、伦理学和美学之应用。他根据康德的说法,认为人的心理机能有知、情、意三方面,对应的是真、善、美,而“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者也”[11]。所以“不通哲学而言教育,与不通物理化学而言工学,不通生理学解剖学而言医学,何以异”[12]。其二,中国哲学之需要。中国哲学缺少系统性,引入西方哲学可以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然吾国古书大率繁散而无纪,残缺而不完,虽有真理,不易寻绎,以视西洋哲学之系统灿然,步伐严整者,其形式上之孰优孰劣,固自不可掩也。”[13]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王国维阐释了中西哲学之不同的原因:“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14]缺少方法论,缺少西学的系统性、思辨性,“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15]。“乏抽象之力者,则用其实而不知其名,其实亦遂漠然无所依,而不能为吾人研究之对象。”[16]正是因为缺少西方哲学的思辨性与系统性,使中国学术研究不能在明晰的概念上进行,所以总是不能摆脱实用而成为独立的分析对象。王国维引入西方哲学,正是为了克服中国思想方式缺少思辨、重实用这一问题。“且定美之标准与文学上之原理者,亦唯可于哲学之一分科之美学中求之。”[17]以美学为文学提供原理,进而为文学成为系统性知识,成为独立学科,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学术划分标准,非出于现实功利目的。章程中文学之所以独立成科,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是进入经学的门径与手段,这一点是王国维所强烈反对的。因为在他看来,学术划分标准不能以实用性为准绳,而是要以学术自身发展规律和自身价值为标准。他强调:“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18]学术终究不是手段,学术的根本目的在于求真,而不在于有用无用,学术只有遵循其自身发展规律,才能够发展起来。所以“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19]。在《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梁启超也曾指出,各省设立的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但实际上存在“有西而无中”“有西文而无西学”的倾向,表现出对实用性的重视而忽视了学术自身的发展。面对这种情况,梁启超指出:“考东西各国,无论何等学校,断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能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20]这一点与王国维的看法相一致,王国维认为要想真正地将中国哲学发扬光大,不是将经学放在什么位置的问题,而是要中西学互通,努力研究西方的学问。“夫尊孔、孟之道,莫若发明光大之,而发明光大之道,又莫若兼究外国之学说。今徒于形式上置经学于各分科大学之首,而不问内容之关系如何,断非所以尊之。”[21]“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22]不论是梁启超还是王国维,对于中西学问之间关系的看法,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23]只不过梁启超等人强调中西兼容的同时,更突出本土文化的基础地位,所以京师大学堂的办学宗旨:“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24]“中学,体也;西学,用也。”[25]而张之洞等人特别强调“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实则也是在西学浪潮中的一种文化担忧,恐怕西学势力过强,而使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失落。但是这种兼习中西的开放思想,却因为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而变得异常复杂。中西之学的融合逐渐衍化为中西古今之争,甚至被简单粗暴地置换成“先进”与“落后”的问题,从而遮蔽了社会文化转型的复杂性与内在连续性。
第三,审美非功利性与“无用之用”。王国维反对将文学工具化,强调艺术与文学的非功利性及其“无用之用”。他运用康德、叔本华以及中国老子和庄子等人的思想来阐明,人生痛苦之本质在于欲望,唯有艺术与文学可以使人得到解脱,“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26]。王国维引用叔本华的学说,认为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就有形而上学的需要。所以不论古今中西,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都需要有一种哲学。也就是说,人于生活之欲外,还有知识与感情的追求,“感情之最高满足,必求之文学、美术;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27]。所以不可以用实际生活中的“有用”“无用”来作为标准,而要看到“无用之用”这一层面。对于将文学作为教育手段与经学门径的实用主义观点,王国维指出:“又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故欲学术之发达 ,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28]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特征之一就是文史哲不分,很多典籍既是文学,也是经学与哲学。王国维认为,虽然文学与哲学运行机制不同,诗歌诉诸直观、顿悟,而哲学诉诸概念、理性。但是它们在根本上又具有一致性,即都试图解决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所以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他开篇就指出:“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学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惟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29]因此,哲学与文学并非无用,反而是有大用,并且还不是一时一世之用,而是具有超越性价值。这里所谓的“真理”实际上强调的正是文学、哲学与人生的密切关联,或者说是作为人生慰藉的根本功能。这是任何时代人类都要面对的问题,所以人心一日存,文学与哲学就不会消亡,都会有其“神圣之位置”。
最后,王国维给出了自己的学科设置方案:“合经学科大学于文学科大学中,而定文学科大学之各科为五:一、经学科,二、理学科,三、史学科,四、中国文学科,五、外国文学科(此科可先置英、德、法三国,以后再及各国)。”[30]其中“中国文学科科目”为:“(一)哲学概论;(二)中国哲学史;(三)西洋哲学史;(四)中国文学史;(五)西洋文学史;(六)心理学;(七)名学;(八)美学;(九)中国史;(十)教育学;(十一)外国文。”[31]
李泽厚谈到严复的贡献时曾说:“严复从一开头就非常重视哲学认识论。他提到哲学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考察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整个问题,并明确认定认识论是关键所在,这才是严复思想一个很突出的地方。”[32]同样,王国维引入西方哲学对中国美学、文学批评及史学都有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他还不满于严复在哲学上重经验论及实用性,而轻视理论思辨与形而上学。他自觉地以康德、叔本华等欧陆哲学理论作为方法论和认识论,来武装中国人的头脑,为中国近代学术及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方法与新的眼光。正如批评家李长之所指出:“即使我们承认王国维是中国第一个批评家,也并不夸张。他仿佛是中国快要有像样的批评家的先导,我们不由得不对他施以最虔诚的敬礼。”[33]
1912年,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第一次提出了废除经学,将其归入哲学、史学和文学的改革思想。1913年民国教育部发布了《大学规程》,正式将文学、历史和哲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确立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方案。到1919年朱希祖《文学论》的出现,建基于美学与文学原理的文学学科才真正得以实现。
三、学院批评与知识生产
朱希祖是著名的史学家,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与钱玄同、鲁迅、周作人、许寿裳等人受业于章太炎。1913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朱希祖时任国文研究所主任,与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学。1920年他与郑振铎、沈雁冰等十二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对于朱希祖,人们经常因为其历史学方面的贡献而忽视了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从文学研究体制的角度看,他的《文学论》可谓是完全按照西方美学与文学理论来系统阐释文学性质的开山之作。其主要讨论的问题可以概括为: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理论内涵与学理根据,探寻“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独立之资格”。
第一,作为学科的文学。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就要有独立的文学观念,而传统杂文学观显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吾国之论文学者,往往以文字为准,骈散有争,文辞有争,皆不离乎此域;而文学之所以与他学科并立,具有独立之资格、极深之基础,与其巨大之作用、美妙之精神,则置而不论。故文学之观念,往往浑而不析,偏而不全”[34]。朱希祖受业于章太炎,而章太炎的文学观恰恰是传统文学观的代表,他认为一切著于竹帛的文字,有无句读皆称之为文学。这样一来,所有学术就都被文学这个概念给囊括了。所以中国学术要发展,就应该按照不同学科的特性分科,将各个学科独立开来。而如同前文讨论王国维引进西方哲学时所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并不长于这一方面,学科独立不得不“取材欧美”,“取其治学之术以整理吾国之学”[35],这样才能克服“仅为政治之附庸”的旧观念,找到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根据。
第二,“主情”与“纯文学”的概念。朱希祖认为从刘勰《文心雕龙》到章太炎的《国故论衡》,都以“作文之法”为文学。但是,这种“文章法式”只是“外事”,即文学的形式层面,而没有深入到“内事”即作品的思想情感,“内事”才是决定文学之为文学的关键。因此造成“有文章而无作用,有艺术而无思想”[36]的原因就在于,“吾中国文学之律令,仅规范夫文学外事之过也”[37]。所以文学之独立不能为他律所支配,要建立在自律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情况下,朱希祖引入了英国培根关于知识分类的观点以及日本太田善男的“纯文学”概念。培根将学术分为三大类即史学、诗学和理学。史学以记忆为主,理学以悟性为主,诗学以想象为主,三者分别独立。而中国文学概念则涵盖一切学术,所以不可不分。太田善男在《文学概论》中指出,诗为主情,为“纯文学”,历史哲理主知,为“杂文学”。根据这一标准,朱希祖将诗赋、词曲、小说、杂文皆归为纯文学。“纯文学”概念对于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型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可以说基本贯穿了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早在1906年,王国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首次使用了“纯文学”“纯美术”概念,而后鲁迅在1908年《摩罗诗力说》中也使用了“纯文学”这一概念。周作人则提出了“纯文章”“美文”概念,梁宗岱提出“纯诗”概念,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向内转”,使“纯文学”再一次成为文学转向的重要内容与参照。只不过不同时期对“纯文学”强调的侧重点略有不同,有时强调文学的语言、形式等文学性问题,有时更强调文学的情感性与审美属性。值得注意的是,朱希祖引入“纯文学”观念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他强调文学革命与文学独立之间不可偏废,互相为用。认为文学革命要想革除艰深的贵族文学而发展通俗易懂的平民文学,离不开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认识。总之,朱希祖引入“纯文学”概念,强调文学“以情为主,以美为归”[38],将王国维所主张的西方现代审美话语,进一步落实到文学研究之中,使文学研究更具科学性与知识性,为文学成为一个稳固的学科,进一步奠定了学理基础。
第三,“美妙精神”与感化人心。根据文学的主情特征,朱希祖提出了以感动多寡来作为文学好坏的评价标准。感动的人越多,文学作品就越成功。这种感动的作用乃是源自“美妙之精神”,“是故精神愈美妙,则感动之力愈强大”[39]。他以尼采的超人哲学与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等学说对人类的重大影响为例,说明其美学的重要影响。由此可见,朱希祖与王国维一样主要也是受到以康德、席勒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美学理论的影响。另外,朱希祖也很重视文学的美育功能。“得以最浅近之语言输最高美之情感,此可以鼓动一世而为感化大同之利器也”[40]。强调文学之用在于感化人心,而这种感化又是不知不觉中完成的,这正是文学潜移默化的陶养作用。
朱希祖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他在大学体制之中讲授文学原理,讨论文学的性质与边界,自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意味着文学研究以知识化形态被传授,同时也意味一种批评形态即学院批评的形成。这种批评以系统化、理论化与知识化的方式,真正使文学以知识生产的方式成为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成为文学研究与学科发展的新机制。至此,文学学科的发展基本完成了由“致用”向“立知”的转变。
对于20世纪初文学立科的根据,我们当然可以从社会、历史角度来解释这种巨大变化,分析其立科的社会条件。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文学的性质特征入手,由内到外地讨论文学立科所必须具备的学理基础。现代中国文学立科既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制度上的回应,也是文化转型、文学自身发展的全面调整。从经学到美学,从“经世致用”到“无用之用”,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逐渐让位于审美特性,文学观念也逐渐由杂文学观向美的文学观念转变。伊格尔顿说:“当宗教逐渐停止提供可使一个动荡的阶级社会借以融为一体的社会‘粘合剂’、感情价值和基本神话的时候,‘英国文学’被构成为一个学科,从维多利亚时代起继续承担这一意识形态任务。”[41]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当经学被废除以后,中国文学被构成了一个学科,继续发挥着经学所承担的意识形态的任务。从“致用”到“立知”,在立科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两种对抗的力量,也几乎贯穿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工具论与自律论,为艺术与为人生,意识形态性与审美自制等问题始终复杂地纠缠在一起。
当下,文学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20世纪上半叶及80年代相比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以后,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也逐渐成为关于文学的知识传授与知识生产。可以说,文学学科的发展在知识化的路线上已然越走越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重新讨论文学立科的过程,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即文学学科的发展不仅要有静观的“立知”精神,也要有通过文字来介入日常生活的能力。而这后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学科设置中的“致用”精神,通过培养学生的“作文”能力,来恢复文学研究、文学教育与日常生活的感性联系。这也就是说,虽然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对文以载道与杂文学观的批判,离不开对审美非功利性话语的引入,但是随着社会与文学自身的发展,将文学限制在美学或某种知识的范围内,显然已经暴露出诸多问题。在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时代,在人人都是批评家的时代,也许“写”比“看”更值得玩味。而这种“写”并非一定是文学创作或论文写作,可以是日记、信札、公文,或者在朋友圈、微博、抖音等自媒体上发布的一段生活随想,等等。总之,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所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知识,还要有通过文字来介入日常经验的写作能力。在“知”与“用”、“看”与“写”之间,去体会非功利的愉悦,去进行情感的净化,去创造与欣赏生活的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微时代’文艺批评研究”(项目编号:19ZD02)阶段性成果]
[1] 李怡主编《词语的历史与思想的嬗变》,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38页。
[2] [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9页。
[3] 参见陈国球《文学如何成为知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9页。
[4][5][6][7][8][9][10][20][24][25]王杰、祝士明编《学府典章: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初创之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页,第219页,第220页,第220页,第 254页,第 254页,第205页,第148-149页,第112页,第149页。
[11][12][13][14][15][16][17][18][19][21][22][23][26][27][28][29][30][31]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周锡山评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51页,第151页,第152页,第131页,第132页,第132页,第114页,第126-127页,第245页,第115页,第113页,第247页,第4页,第111-112页,第125页,第89页,第116页,第116页。
[32]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75页。
[33]李长之《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李长之文集》第七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页。
[34][35][36][37][38][39][40] 朱希祖《朱希祖文存》,周文玖选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第46页,第48页,第48页,第50页,第53页,第52页。
[41][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页。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