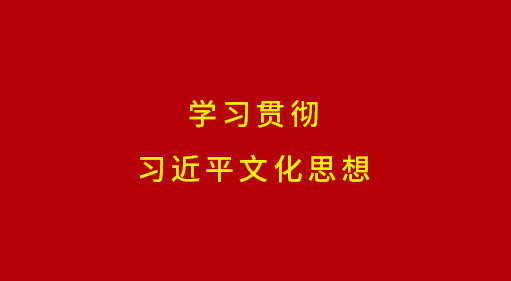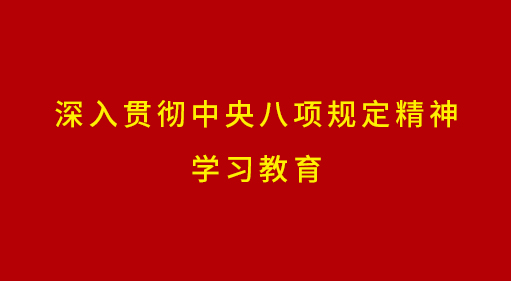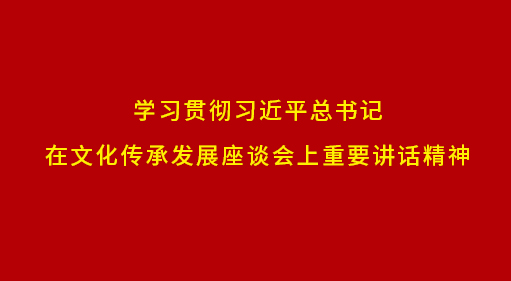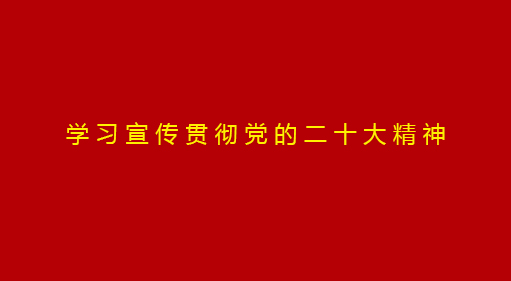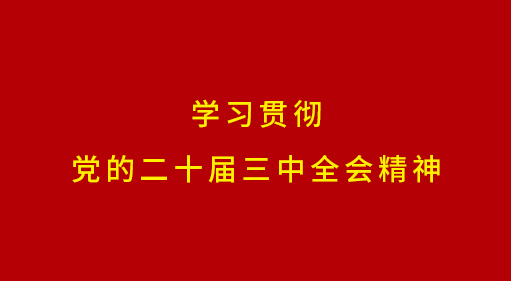从“80后”到“90后”: 以青春文学激发青少年创意写作的思考
时间:2024-03-11
孙桂荣 李沐杉
摘 要:“80后”青春文学的发生、流变及其从主流文学体制中的逸出本身,是青少年创意写作在21世纪中国蓬勃兴起的结果。该结果又能作为一种文学潮流以其强大的文化吸引力、辐射力对青少年创意写作产生影响。从“80后”到“90后”,青春文学体现了由“酷”青春、“绚”青春向“暖”青春、“治愈系”的转变,为以此激发青少年创意写作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充分的价值资源。将青春文学纳入创意写作中来的范式构想包括“写作式阅读”理念的建立、“由仿到创”工坊设计、情景式动态化写作活动架构等等。
关键词:青春文学;“80后”;“90后”;青少年创意写作
创意写作是突破传统叙事成规、熔铸个性才情的创造性写作,青少年创意写作是将青少年青春期成长、自我探索、主体生成等元素融入其中的创意写作。如果说文化创意产业是全球化背景下以文化创造力提升为诉求的新兴产业,青少年创意写作便是这一新兴产业中的一个核心环节。青少年创意写作近年来在中国的兴起与兴盛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形成了“面向文化产业的大众化培养”与“面向文学生产的精英化培养”等不同的创意写作了理论范式[1]。不过,目前的青少年创意写作研究还较为笼统、模糊,在从哪个层面、如何践行创意写作问题上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具体化论述还不是太多,尤其缺乏以具体文学现象为依托进行的创意写作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一、青少年创意写作与“80后”青春文学的发生
青春文学是以校园、青春、成长等为关键词的文学写作。应该说,任何一个年代都有表现这些元素的作品,不过,其能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类种(有着相当数量的作者群和读者群、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相对独立的传播流通渠道)的出现,却主要发生在近一二十年。目前所说的青春文学一般是从新世纪前后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80后”文学开始的。
2006年,批评家白烨在《“80后”的现状与未来》中提出了一个流传甚广的观点:“‘80后’走进了市场,却没有走上文坛”,作为当时“80后”写作代表的韩寒以博客为阵地、以粉丝为后援,与白烨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论战,并最终演绎成了一个可以纳入文学史的“韩白之争”事件。什么是“文坛”,谁有权力界定“文坛”,“市场”与“文坛”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这一系列本来属于文艺理论范畴的学理问题在论战中“出圈”,成了公众由此了解文学与创意产业关系的一个媒介性话题。不过,当年的人们把注意力更多放到了“80后”青春文学与主流文学体制的龃龉上,像武汉大学昌切教授在评论这件事时认为,“今后中国将出现两个文坛,一个是以人民文学出版社、《收获》杂志、作家协会等构成的传统文坛,一个是以网络为核心的‘80后’文坛”[2]。时至今日,“市场”与“文坛”的关系已不再像十多年前那样泾渭分明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收获》杂志、作家协会等代表的主流文学机构触电、上网已经成了新常态,甚至本身成了融媒体的一部分,而作为市场化代表的网络文学阵地有时也会诞生一定程度上的严肃文学。用这种“后视性”眼光回望当年的“韩白”之争并不是要为双方分出孰优孰劣,而是指出“80后”文学的产业属性这一点在当时被精英文学观与大众文学观的意气之争所遮蔽,并未得到学界认真与足够的对待,这当然也与当时的文化与文学语境尚不足以支撑纯粹创意产业角度的“80后”青春文学探讨有关。在青春文学从“80后”到“90后”、再到“00后”,不但作品辈出、社会影响力方面也愈益做大做强的今天,笔者认为应对“80后”青春文学的存在价值与文化理路进行重新审视和考量,将其文本构成、创作风貌、传播路径等纳入青少年创意写作中来考察是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由此可以在理论与实践上实现“80后”青春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的双重开拓:既以创意写作的教育教学视角拓展“80后”青春文学研究领地,又能以“80后”青春文学的文本创作与文化产业实践开拓青少年创意写作研究空间。
的确,“80后”青春文学从诞生之初就带有与传统青少年写作理念差别很大的创意写作意味。像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作者是借助“新概念”作文大赛脱颖而出的,而“新概念”作文大赛从1998年第一届开始就提出了“两新一真”理念——“新思维”(创造性、发散性思维,打破旧观念、旧规范的束缚,打破僵化保守、提倡无拘无束)、“新表达”(不受题材、体裁限制,使用属于自己的充满个性的语言,反对套话,反对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真体验”(真实、真诚、真挚地关注、感受、体察生活),其对不同于传统命题式、概念式、教条式作文的创造性书写的推崇与创意写作在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而创意写作,根据葛红兵、许道军的界定,“最初仅仅是指文学写作和文学写作教育,后来泛指包括文学写作在内的一切面向现代文化创意产业以及适应文学民主化、文化多样化、传媒技术的更新换代等多种形式的写作”[3]。青春文学与畅销书、影视改编、流行歌曲等文化创意产业的联系异常紧密,像《悲伤逆流成河》《左耳》《你好,旧时光》《最好的我们》《致我们终将失去的青春》《匆匆那年》《谁的青春不迷茫》等近年来热映的青春电影几乎都是青春文学改编的。创意写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包容也意味着与作为创意产业重要一环的青春文学的耦合。而得益于青春文学独特青少年受众的庞大市场消费能力,其文学产业化的程度相比一般网络文学甚至都要高。那些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青春文本有着鲜明而独特的创意性色彩自不待言。
可以说,“80后”青春文学的发生及其从主流文学体制中的逸出,这一现象背后便是青少年创意写作在21世纪中国蓬勃兴起的结果。“80后”青春文学是典型的低龄写作,是青少年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的表现,不少写作者的成名作是在大学,甚至中学阶段完成的,像韩寒《杯中窥影》、郭敬明《幻城》、张悦然《小染》《黑猫不睡》等新概念作文大赛得主的早期作品不少都是在中学、大学的求学阶段完成的。而在受众层面,低龄化,甚至越来越低龄化的现象也很明显。据统计,2016年青春文学的图书销售额曾占到整个图书市场的37.04%,最近几年来受网络、影视等大众文化的冲击有所下滑,但也占到25%以上[4]。而在这些读者之中作为中学生的青少年占了很大比例,像89%的中学生表示看过青春文学作品,51%的中学生对青春文学作者关注或非常关注[5]。青春文学作者群和读者群都相对集中地稳定在青少年群体中的这种特性,是其他文学类种难以比拟的。这为青春文学以其强大的文化吸引力、辐射力对广大青少年创意写作能力的激发与提升创设了条件,也为推动创意写作理念向大、中学青少年群体延伸提供了可能性。
当然,相比一般意义上的创意写作,青少年创意写作不仅仅是写作技能的问题,还与青春、成长、人生等生命姿态紧密相连,有着特别的伦理意义。“写作就是生活、语文就是成长”[6],可谓是对它的最好概括。但是,“80后”青春文学是一种有争议的文学现象,曾因为思想上的单薄偏执、艺术上的清浅刻意、传播上的商业化运作而广受诟病,其能够担当起激发创意写作的大任吗?尤其是面对一群价值观、人生观正在形成的青少年。笔者认为这样的疑问是可以理解的,但并非是无法解决的。考虑到青春文学对青少年心理的贴近,尤其是其近年来的发展、流变,以青春文学激发青少年创意写作是既有一定理论可能性,又有一定实践可行性的。近年来青春文学从“80后”到“90后”发展谱系的梳理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问题。
二、“从80后”到“90后”:创意写作视角下的青春文学发展
新世纪初年,“80后”文学的横空出世改变了年轻一代文学新人的“入场”方式是毋庸置疑的,“80后”一代的书写活动由此也开启了当代文坛的青春文学之旅,但青春文学如何向前发展、如何与包括主流文学在内的社会文化机制遇合碰撞却是与更低龄的“90后”“00后”推动分不开的。目前大批“00后”也开始尝试写作,《2022中国科幻网络文学白皮书》《2022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首次创作便选择科幻题材的作者里72%为00后”[7],但因为年龄太小、同质化明显,给人留下殊异印象者还不多见,学界所说的青春文学主要指的还是“80后”“90后”。本文也是在这一层面上言说青春文学的,笔者认为经过近20年的发展,青春文学从“80后”到“90后”在内容、形式及与主流文坛的关系上均已发生了一定变化,而这成为其之所以能够推进青少年创意写作的现实基础。
在从“80后”一代笔下的青春文学书写到“90后”一代的代际发展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生成机制层面的微妙变化。“80后”文学被社会瞩目的过程是伴随着“韩白之争”“陶玄之争”等与主流文学体制的撕裂而来的,笔者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将“80后”一代的文学入场式称之为“断裂的青春表演”,其是一种割裂传统文学体制的“自下而上”式生成, 其“‘青少年书写、并由青少年热衷的传播媒体/传播方式抵达青少年读者’的三位一体运作模式对于青春文学而言有某种前瞻和预言性”[8]。这对于韩寒、郭敬明等赢得文学市场化先机的作家来说是适用的。但对于“90后”一代青春文学写作者而言,却未必完全适用。一方面,青春文学市场经过十多年的运作积淀,已相对成熟规范,单凭市场化运作就引发社会瞩目的难度增加了;另一方面,主流文学机制也逐渐开始将扶植文学新人的传统任务落实到了低龄写作者身上。因此,目前比较活跃的“90后”写作者在文学机制上是比较驳杂的,固然不乏像卢思浩、张皓宸、苑子文、苑子豪等通过写作青春文学畅销书成名的资本运作型作家,但还有更多主流文学机制提携的写作者,像居于文学界“国刊”之位的《人民文学》杂志从2017年第1期到2022年第3期,在连续5年的时间里开办“九○后”专栏,推介了李唐、庞羽、国生、郑在欢、王苏辛等37人。另外,《山花》《天涯》《上海文学》《青春文学》《芙蓉》《大家》《福建文学》等大批主流文学期刊均在2017年前后纷纷刊登“90后”写作者的作品。可以说,在与主流文学机制的联系上,“90后”青春文学写作者显然要比“80后”一代更紧密些。
从“80后”文学到“90后”文学的青春叙述格调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21世纪初的“80后”青春文学曾被视为“问题写作”受到不少人的担忧。的确,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愤青式叛逆,“以病为美、以悲为美”的刻意忧伤,虐心虐恋的极端化情节与极端化人物等,在韩寒、春树、郭敬明、张悦然等人的写作中曾反复出现过。“‘问题写作’怎么成了‘偶像写作’”的质问在社会上曾引起广泛共鸣。不过,据笔者观察,近年来流传较广的以“90后”为主要写作者的青春文学读本在对青春的叙述基调上已有了较大的调整,无限放大青春期某种特定心理的极端题材、极端人物少了,生活化、常态化的青春书写多了起来。像不同于韩寒《像少年啦飞驰》、春树《北京娃娃》、李傻傻《红X》等以叛逆、疯狂、沉沦、性、犯罪、流浪等现实中的边缘人与边缘事件表达青春期张扬纵恣的边缘化极端体验,冯唐《万物生长》、九夜茴《匆匆那年》、八月长安《最好的我们》、苑子豪《我不怕这漫长黑夜》等近年来的青春书写,已然将写作重心放到了“校园”这种青少年最经常的生活环境中,青春期的叛逆情绪也融汇到了青少年友情、爱情、亲情等的日常书写中,生活化氛围明显增强。情感描写上,郭敬明《悲伤逆流成河》《梦里花落知多少》、张悦然《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等生生死死、大喜大悲、大爱大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忧伤虐恋、“一悲到底”也少了。在八月长安《你好,旧时光》、赵乾乾《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张嘉佳《云边有个小卖部》等作品中,日常人性的现世情怀、俗世的幸福感和治愈感是比较明显的,主人公往往能够以一颗向真、向善的心谋求与生活的和解和对他人的理解,爱情的结局也往往是美好的、给人希望的。乃至有研究者发现青春文学出现了由“冷”到“暖”、由“残酷青春”向“微笑青春”的转向[9]。
这种“转向”对创意写作最大的影响是,青春文学在与大多数青少年青春期经历的常理、常情、常态切近的同时,也能够在一定层面上发挥正向教育功能,以相对明朗、阳光的书写影响青少年正在生成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有的还发挥了鲜明“励志”价值。像苑子文、苑子豪《我们都一样,年轻又彷徨》中对学习生活的写照:“一到上课我就拿着红、黑、蓝三种不同颜色的笔在手边两个笔记本上写写画画”,“整整十二个笔记本,十个错题本,叠起来连夹子都夹不住的习题册和试卷”,“深夜围着田径场一圈圈跑却不知道疲惫是什么滋味,大半夜不睡觉偷偷爬起来在阳台上背英语背到哭,桌上写着‘北京大学’四个字的梦想字条撕了又贴。”[10]有过高中经历的人就会知道这些细节并不是什么文学想象,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本身,创意写作的“生活作文”、“语文是成长”等原则在这些描写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又如《我不怕这漫长黑夜》中身患白血病的苟延东觉得生命走到了尽头,后来却得到了医生误诊的消息,故事最后,作者借主人公母亲之口写道:“每一次失望透顶的时候,都会有一颗星星为你点亮,但你要睁开眼,才能看得见。”[11]这种哲理性的励志书写是能够助益青少年向前、向上成长的。还如苦口婆心的情感分析:“失恋给你的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一个中途停下的时间,让你好好思考到底该如何走完它。我们拥抱和推搡,我们亲吻和冷眼,我们同时拥有一个世界和失去一个世界。他日相逢,用沉默还给沉默,然后在缱绻不尽的爱里,勇敢生活。”[12]青春文学的这些言说对实现青少年创意写作将生命、自我、价值观生成融入其中的伦理价值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当然,青春文学能够激发青少年创意写作的最大的利器还是其在语言、意境、意象、修辞等层面的美学功能。不管是早期“80后”的“酷”青春、“绚”青春,还是后来“90后”的“暖”青春、“治愈系”,青春文学或讥诮或凌厉、或清丽或明媚、或洒脱或蕴藉的花式表达,混合着浅浅的哲理、淡淡的伤感、浓浓的诗意等特有的青春物语,能够为青少年创意写作提供很好的研习材料。像修辞上的通感与反讽:“语文书里作者文章的主题立意仿佛保守男女的爱情,隐隐约约觉得有那么一点,却又深藏着不露;学生要探明主题辛苦得像挖掘古文物,先要去掉厚厚的泥,再拂掉层层的灰,古文物出土后还要加以保护,碰上大一点的更要粉刷修补,累不堪言”[13];意象的智性跃动:“原来,思念像是影子,你逃得越快,它就跟得越紧,连夜晚它都不放过。你关了灯,它就住到你的心里”[14];表达的奇谲润泽:“高中的时候,她坐在我眼角将将能扫到的位置。如果她是一种植物,我的眼光就是水,这样浇灌了三年,或许她从来没有想过她如此湿润的原因”[15];情感的恣意通透,“终于你也懂了,自己之所以会想念他,其实并不是因为他的好,而是因为,之后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觉得好,你怀念的,自始至终,都是爱或被爱的滋味”[16];景物的绚烂灵动,“是春了……万物萌动的声音,哗哗,噗噗,一个世界坐不住了,该发芽的,发芽了,该开花的,开花了”[17];等等。事实上,由于时代的久远,经典文学(像古诗词、古文、半文半白的民国文章等)的语言更适合吟诵、鉴赏、研究,而非在日常生活中模仿、言说、写作。对比鲜明的是,当下人以当下语言描写当下生活的青春文学,却能够为青少年创意写作提供更多的仿写资源。而这一点,也恰恰是当今青少年所翘首企盼的。数据显示,半数以上受访学生认为青春文学对语文有影响,而92%的学生表示课堂上听不到老师讲解青春文学作品,76%的人希望青春文学能够纳入学校教育中去[18]。借鉴高校中的创意写作教学经验,探索以青春文学激发青少年创意写作的组织形式、方法策略等,是对近年来青春文学发展的一种吸纳和认同,也是呼应青少年创意写作需求的一种顺应时势之举。
三、将青春文学纳入创意写作的范式构想
从“80后”到“90后”,青春文学迎来了自身近乎脱胎换骨的变化,也为其与青少年创意写作的文化联结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目前,青春文学因为非经典化的存在,经常处于青少年自发、私下,甚至“偷偷”阅读的状态中,流于散漫、匆忙、一次性的“浅阅读”者居多,在实践层面上对青少年创意写作的激发尚处于尝试探索阶段。笔者认为将青少年对青春文学的阅读兴趣转化成对其创意写作能力的激发与提升是问题的关键,可以从这样几个层面构建以青春文学为中心的青少年创意写作范式。
(一)“写作式阅读”理念的建立
“写作式阅读”(writerly reading)是像作家一样关注文本如何生成、如何表达的“创意阅读”。研究者发现,“创意写作教学法的基础性规则包括:一个写作的创意写作作家、写作式阅读、写作共同体、用于作品创作和修改的讨论”[19]。“写作式阅读”是以写作为中心的阅读,阅读为写作服务是其根本特征。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书写目的、阅读者主体意识不强,只是“为读而读”的话,创意写作的效果并不好。阅读量越大,反而越容易形成布鲁姆所说的被前人或经典文本所左右的“影响的焦虑”;阅读得越杂,题材、主旨、风格迥异的文本彼此打架,越会搅乱阅读者思绪;阅读得越“专业”,越容易被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理路语感等带节奏。牢记“阅读的目的是为写作”,从有利于自身文学创作出发选择阅读对象、阅读方法才不会自乱阵脚,这也是“写作式阅读”理念的初衷。
变“阅读本位”为“写作本位”,将漫不经心、囫囵吞枣、随手翻似的随意散漫阅读“指向言语表现,指向写作,指向读写互动,以写作为依归”[20]的“写作式阅读”,是激发青少年创意写作的第一步。而青春文学尚未被经典化、权威性不高,而且作品内容与形式上有太多契合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当下性、时尚性特点,使得它比历史上的经典文学更容易激发青少年进入“我也可以写”的创作冲动。青少年带着“我能写、我愿写、我要写”的目标去阅读青春文学,既有利于从阅读中捕捉到有利于写作的信息,又能惠及青春文学的阅读效果,因为不同于随意散漫的浅阅读,“如果读之前以写作为目的……思维便沉潜而活跃,心情便宁静而兴奋,概念、语言、情思纷至沓来,汹涌的思维活动便纳入了稳健、恰当的写作运思与表达之中,阅读记忆就不再是过眼云烟”[21]。这种阅读当然更容易转化为有效的写作实践,不但有利于破除“写作天才论”、树立“人人都可以写作”的创意写作理念,还能助益青少年修正目前青春文学“读得多、但读不好”的不良格局。
(二)由“仿”到“创”的工坊设计
创意写作一般采用“工作坊+过程教学法”的培养方式。汤姆·吉利曾言,创意写作工作坊“每节课尝试完成三件事:一个关于写作的演讲,一个关于文本的讨论,一个课堂写作任务(小组任务或者介绍一个新任务)”[22]。上海大学“故事写作”课程则“包括故事知识与技巧研讨、同伴作品工坊评议、课堂写作三个部分”[23],这些创意写作教学策略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与高校创意写作教学以激发学生原创意识不同,青少年创意写作因为学生尚处于文学启蒙阶段,以既有文本为“拐杖”、在“写作式阅读”中酝酿的仿写、续写、改写、重写等工坊设计,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创意写作的实践性效果。
以作为晚近“治愈系”青春文学代表的张嘉佳《云边有个小卖部》为例,谈一下这种由“仿”到“创”的工坊设计。“仿写”是大到文章结构、情节设定、人物形象塑造,小到词语、修辞、句式等“模仿式”的写作,因为融入了自己的感悟与经验,写出来的并不会与原文一样。像对照《云边有个小卖部》第一章仿写出自己心目中“美”与“苦”的云边镇,这对意境的营造、意象的熏染、氛围的烘托等写作基本功锤炼是十分有益的。“续写”是对原文的延伸性书写,比较符合青少年读过一本书后意犹未尽、浮想联翩的心理,像小说中的刘十三,在外婆与程霜永远离开他、到另一个世界之后会怎样?假如与牡丹、平头邂逅后是要戏剧性地报仇雪耻还是显示出成长后的达观?“改写”是对原文本某些元素的挪用、改换、变动,像女同学将自我代入,把主人公的刘十三性别改为女性,人物关系就会发生很大改动。或放大原文省略掉的刘十三走出故乡后云边镇发生的事情,将外婆、程霜的小镇生活进行想象性还原等。“重写”另起炉灶的意味更明显些,是只取原文中的一个场景、一个桥段、一种氛围,以天马行空的想象恣意铺染。像从少年刘十三怨乡又恋乡、离乡又归乡中寻找自己的成长踪迹,创作出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物关系与故事走向,描写自己成长世界的残酷和温暖。还如对小说“‘失败少年’返乡找到情感慰藉”的主题推倒重来,描写少年刘十三如何付出种种代价在城里扎下根却发现“有家难回”的青春伤痛,“‘失败少年’返乡找到情感慰藉”变身“‘成功少年’离乡难觅初心”,这种重写已接近了青春文学的原创。
(三)情景式、动态化的写作活动架构
“工作坊的形式比较灵活,可以走出教室,采取田野采风、写作(夏令营、冬令营)、户外活动、实地考察等形式”[24]。依据写作对象的具体特色,在社团、兴趣小组、课外活动中进行的情景式、动态化写作,是最适合青少年的创意写作方式。青春文学阅读十分灵活,完全可以在特定语境下展开。像丁立梅《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暗香》《有美一朵,向晚生香》等文本中的花卉世界,紫薇花、绣球花、蔷薇花、月季花、水仙花、凤仙花、油菜花……应有尽有、美不胜收,青少年可以在户外美景中欣赏美文,书里书外相呼应。破冰、开脑、激活、修改、孵化等创意写作工坊“三阶六维教学法”[25],可以在情景式、动态化活动中被青少年有意无意地吸收、践行。还可以进行“大中衔接”的创意写作尝试,广义的青少年包括大中学生,他们也正是青春文学的忠实读者与热心创作者。受过创意写作训练或有青春文学创作经验的大学生可以到中学作为工坊主持人、组织者,既能为大学生实习、社会实践提供机遇,又能解决中学生的青春文学“领读员”“点拨者”稀缺的矛盾。青少年创意写作除了与高校创意写作联盟外,还可以走社会化路子,与艺术培训、作家工作室、社区服务、各种社会团体等合作,写作“从娃娃抓起”,为有文学创作意愿、兴趣和才能的青少年提供良好的教育教学资源。
可以说,从“80后”到“90后”(以后会顺延至“00后”“10后”等)的青春文学发展为青少年创意写作提供了充沛的阅读、摹写资源,而青少年丰富多彩的创意写作实践活动反过来又会内在地提升青春文学的艺术品格,这是一个双向互动互赢的过程。当然,在这其中也需要注意青春文学读本的辨析筛选、避免工作坊教学流于表面、警惕商业动机的濡染等系列问题。以青春文学激发青少年创意写作的问题目前还处于实验、构想阶段,本文的写作就是想起到这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基金项目: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青春文学阅读与初中生作文能力培养研究”(项目编号:YZ2019049)阶段性成果]
[1] 叶炜、王军雨《中国大陆创意写作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写作》2018年第7期。
[2] 梦情《80后作家:十年前占领市场,十年后占领文坛!》,网易2023年10月20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DKVQ92QD0521A5DS.html.
[3] 葛红兵、许道军《创意写作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4] 出版人杂志《码洋、品种持续萎缩,谁能拯救青春文学市场》,搜狐2023年10月20日, https://www.sohu.com/a/247137668_211393.
[5][18] 参见于丹丹、魏冬《由青春文学对中学生的影响探索“三结合”教育网络建设新路》,《文教资料》2010年第8期。
[6] 叶炜《美国中小学写作教育与中国创意写作的未来》,《语文教学通讯》2021年第18期。
[7] 许旸《新动能来袭!95后00后正涌入科幻网文写作》,《文汇报》2023年5月25日。
[8] 孙桂荣《从“70后”到“80后”:断裂的青春表演》,《上海文学》2010年第9期。
[9] 参见孙晴《从“残酷青春”到“微笑青春”——网络时代青春叙事的转变》,《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7期。
[10]苑子文、苑子豪《我们都一样,年轻又彷徨》,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74页。
[11]苑子豪《我不怕这漫长黑夜》,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49页。
[12]杨杨、张皓宸《你是最好的自己》,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13]韩寒《三重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14][16]肆一《想念,却不想见的人》,应届毕业生网2020年8月15日,https://www.yjbys.com/yulu/qinggan/3575.html.
[15]冯唐《万物生长》,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17]丁立梅《有美一朵,向晚生香》(散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290页。
[19]许道军《“像作家一样读书”:从新批评到创意阅读——创意写作活动中的阅读研究》,《当代文坛》2019年第1期。
[20]许道军《创意写作的本相及其对立面》,《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19)》,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30页。
[21]潘新和《潘新和谈语文教育》,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
[22]葛红兵、许道军《创意写作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23]许道军《“作家如何被培养”——作为教学法的创意写作工作坊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24]许道军《创意写作:课程模式与训练方法》,《湘潭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25]冯现冬《“三阶六维”:创意写作工坊课堂教学过程研究》,《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19)》,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101页。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