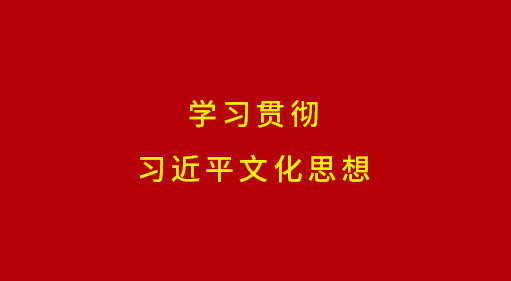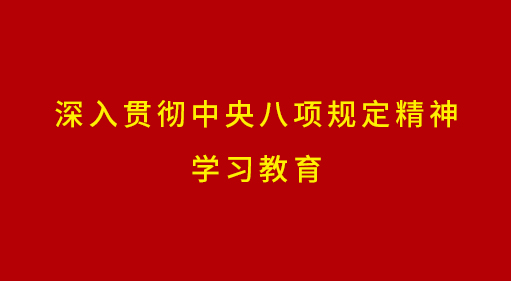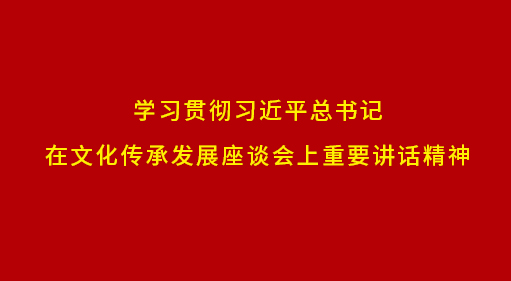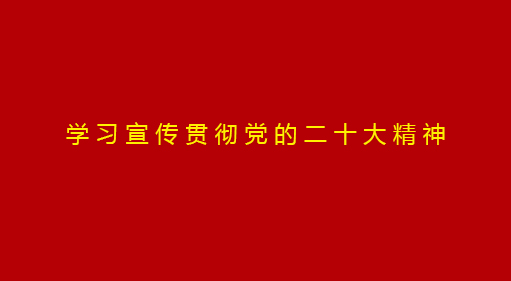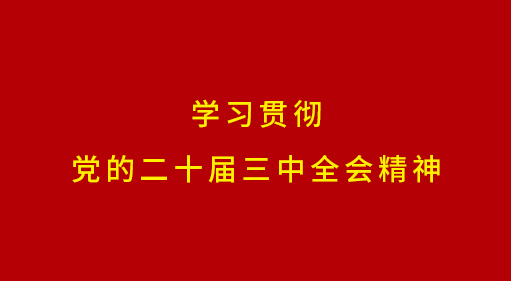非虚构写作的相关概念界定及策略意识 ——从纪实文学的概念出发
时间:2023-11-06
刘 栋
摘 要:美国的“非虚构小说”和“新新闻报道”引入中国后,相继掀起纪实文学和非虚构写作的热潮。20世纪80年代,“Nonfiction Novel”有多种译名,其中纪实文学的概念使用最广,经过发展演变,逐渐变成一种文类概念。2010年后,有关非虚构写作的概念,学界大致分为文体说、文类说和策略说,三种观点相互缠绕,彼此共存。在文体层面,非虚构写作主要指非虚构小说,与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共同成为纪实文学的主要文体;在文类层面,它与纪实文学无太大差异,建议仍用纪实文学的概念。2010年后非虚构写作的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策略层面,它的策略意识主要表现在问题意识、行动意识和跨界意识。
关键词:非虚构写作;非虚构文学;纪实文学
自2010年《人民文学》设立“非虚构”专栏以降,非虚构写作迅速成为一股旋风,席卷整个文坛,并在历史学、新闻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引发连锁反应,至今热度不减。十余年来,非虚构写作及相关概念仍未厘清,这是目前有关非虚构写作研究公认的难题。当下非虚构写作逐渐泛化,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也损耗着自身的主体特性。何平说:“今天很多报告文学的从业者也常用非虚构写作指称他们所写的报告文学,‘非虚构写作’这个带有冒犯和挑战意味的概念,正在慢慢地被‘稀释’掉。”[1]可见,有关非虚构写作的概念不应该被搁置,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才是当下应有的态度。
《人民文学》在倡导非虚构写作时,虽不能为其划清界限,但声明一定“不等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2]。不少学者针对非虚构写作与报告文学两个概念进行辨析,也有学者对非虚构写作与特稿、散文等相关文体的关系进行讨论[3],唯独对非虚构写作与纪实文学的关系,要么不谈要么混为一谈。实际上,纪实文学的概念与非虚构写作一样,都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并在国内红极一时,两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试图从纪实文学的概念出发,来重新审视当下非虚构写作的相关概念。
一、纪实文学:“非虚构”的前世面孔
目前国内学者大都将非虚构写作追溯到美国六七十年代的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和新新闻报道(New Journalism)[4],纪实文学的概念也可追溯于此。20世纪70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非虚构”的概念传入中国[5],并在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先后掀起纪实文学和非虚构写作的热潮。在《人民文学》倡导之前,“非虚构”更多以“纪实文学”的面孔出现,此前国内虽有非虚构小说和非虚构文学的概念,但并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与“非虚构小说”的概念一样,“纪实文学”的概念也由“Nonfiction Novel”翻译来,在当时作为一种用小说手法写真人真事的文体。20世纪80年代,“Nonfiction Novel”传入后有多种翻译方式,如“非小说”“报告小说”“纪实小说”“非虚构小说”“纪实文学”或“非虚构文学”等概念。最早将“Nonfiction Novel”引入国内的是董鼎山。他在《所谓“非虚构小说”》中首次对美国的非虚构小说和新新闻报道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6]。随后国内许多学者都注意到美国的非虚构小说和新新闻报道,但对其有不同的称呼,例如,刘茵和理由就将其称为“非小说”[7]。同时,国内产生大量类似于美国的非虚构小说和新新闻报道的作品,它们用小说技巧来写真人真事,被称为“报告小说”“纪实小说”或“纪实文学”。《当代》杂志推出刘亚洲的《惊心动魄……女人的名字是“弱者”吗?》时,作者称之为“报告小说”[8]。其他杂志也开始刊登报告小说。《人民文学》也在不久后连续发表刘心武的《5·19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并标为“纪实小说”,在当时影响较大。紧接着,《收获》《十月》也设立“纪实文学”专栏,并发表作品。这些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同时出现,虽然杂乱,在当时也引起不小的争议,例如朱寨、刘茵和李炳银等学者在《光明日报》对“报告小说”概念展开激烈讨论[9],但都指向美国的非虚构小说和新新闻报道。
在争议的同时,学界已经注意到这些概念内在的联系。俞珑在《“纪实文学”创作述评》中发现,当时中国大量称为“纪实文学”“报告小说”或“纪实小说”的作品其实就是美国的非虚构小说或新新闻报道[10]。刘思谦认为,这些概念是“Nonfiction Novel”和“New Journalism”的不同译法。她在《小说张开了纪实的翅膀——纪实小说审美特性初探》中说:“它们在杂志上发表的时候,名称很不统一:报告小说、新闻小说、口述实录体文学、纪实小说、新新闻体小说、纪实文学等。这大概与Nonfiction Novel和New journalism这两个词可以有好几种译法有关。”[11]总之,20世纪80年代,“非小说”“非虚构小说”“纪实小说”“报告小说”“非虚构文学”和“纪实文学”等概念都是由“Nonfiction Novel”翻译而成,都指用小说手法写真人真事的文体。当时“纪实文学”的概念被学界大量使用,产生很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纪实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被称为一种策略。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不少作家从小说写作转向纪实文学写作。有论者将当时大量出现的纪实文学作品称为“新纪实小说”,认为这是作家们采取的一种策略。学者杨经建在《“新”纪实小说:一种世纪末的创作策略》中提出“‘新’纪实小说”的概念,并认为这是世纪末的一种“创作策略”[12]。他认为“新”纪实小说是作家在90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所选择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又是积极有为”的一种创作策略,它“逢源于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融通于虚构化原则和非虚构化倾向之中”,“兼容着艺术审美特质和商业文化品性”[13]。之后,由于纪实文学作品过于猎奇化和媚俗化,甚至引发种种官司,在坊间产生不少非议,纪实文学的策略性也随之失效。
纪实文学的概念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啻被视一种文体和策略,更多被视为一种文类概念[14]。1985年,宗原在《关于纪实文学》一文中认为,“凡是具有真实性和文学性的作品,都可以算作纪实文学”,“纪实文学的外延较广,诸如传记、回忆录、报告文学、日记、书信、采访记实,以及写真人真事的叙事小说、纪实小说等等,都可以列入纪实文学之列”[15]。随后,纪实文学的概念在国内被大量使用,并逐渐变成一种文类概念,在学界成为共识。高文升主编的《纪实:文学的时代选择——新时期纪实文学研究》、张瑷的《20世纪纪实文学导论》和刘卓的《纪实文学研究》是,20世纪末以来国内出版的三部较有代表性的纪实文学研究专著,三本专著都认为纪实文学是一种大的文类概念。
综上,纪实文学和非虚构文学的概念一样,都是由“Nonfiction Novel”翻译而来,起初指用小说手法写真人真事的文体,在当时也有策略和文类的指向。21世纪以来,纪实文学逐渐媚俗化,引起不少争议,逐渐被当成一种文类概念,用来统称报告文学、纪实小说、传记文学和口述实录体等所有纪实文体。
二、非虚构写作的三重概念
正是在纪实文学的发展陷于低谷之时,2010年2月,《人民文学》增设“非虚构”专栏。非虚构写作在文学领域迅速发展,并形成热潮。有关非虚构写作的概念,目前学界争议虽大,但大致可分为文体说、文类说与策略说三种观点。
(一)文体说
“文体说”是把非虚构写作或非虚构文学[16]看作一种文体。持此观点者主要以梁鸿为典型代表,也有不从事特稿写作或研究的新闻从业者[17]。梁鸿认为,非虚构文学作为一种概念和文体,“不排斥‘个人性’的存在,是因为作家对‘我’在文本中的位置有新的理解,认为作为作家的‘我’与现实之间是平等甚至是低于现实的存在,而所谓的‘现实’也没有终极的存在,而是有待不断发现的内部风景”[18]。在梁鸿的相关论述中,作者的个人性和主观性介入是非虚构文学十分鲜明的文体特征,这也是非虚构文学区别于报告文学的最大特点。在新闻领域,不少学者和写作者也将非虚构写作视为一种文体。范以锦与匡骏曾有言:“一种被称为‘非虚构写作’的新的新闻文体——特稿,事实上已在新闻界流行,并形成一定的影响力。”[19]新闻领域非虚构写作的兴起受文学领域的影响,但新闻领域早就有特稿写作的传统,当下新闻领域的非虚构写作是以往特稿写作的延续。文学领域和新闻领域的非虚构写作看似距离较远,但都共同指向美国的非虚构小说和新新闻报道。因此,如果说非虚构写作是一种文体,那么具体指非虚构小说(纪实小说)或新闻特稿,即用小说手法写真人真事的文体。
(二)文类说
“文类说”是将非虚构写作或非虚构文学作为大的文类概念来看待,它包括报告文学、非虚构小说(纪实小说)、传记文学和口述实录体等纪实文体。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王晖、南平、丁晓原、何建明、李朝全和刘浏等。王晖和南平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非虚构文学的概念,将其作为报告文学、纪实小说、口述实录体和传记文学等纪实文体的统称,并分为“完全非虚构”和“不完全非虚构”[20]。在《人民文学》倡导的非虚构写作兴起后,王晖继续沿用此观点[21]。丁晓原的《非虚构文学:时代与文体的“互文”》[22]与何建明的《创意写作理念与实践:中国非虚构文学的新契机》[23]等文章所论的“非虚构文学”实际指报告文学,文章将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学的主要文体。不仅是以往报告文学研究者,《人民文学》时任主编李敬泽、副主编邱华栋也同意非虚构文学作为文类的说法。李敬泽说:“至于‘非虚构’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史传文学等等类别的关系,我没有多想,这些事争论起来很费口舌,我宁可说,‘非虚构’可以是个更大的概念,包括和大于上述各种类别。”[24]邱华栋也曾说:“有人问我,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就不算非虚构文学?我回答:算啊,凡是不是虚构的文学,那就是非虚构文学。”[25]由此可知,有关非虚构写作或非虚构文学的概念,争议虽然较大,但它作为一种文类,容纳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和口述实录体等纪实题材,基本是学界共识。
(三)策略说
“策略说”是将非虚构写作视为一种叙事策略,也可称为“姿态说”。持此观点的学者以洪治纲为典型代表,他认为:“‘非虚构’与其说是一种文体概念,还不如说是一种写作姿态,是作家面对历史或现实的介入性写作姿态。”[26]早在非虚构写作兴起之初,张文东就说:“我认为非虚构是一种创新的叙事策略或模式,这种写作在模糊了文学(小说)与历史、纪实(原文为记实)之间界限的意义上,生成了一种具有‘中间性’的新的叙事方式。”[27]类似地,李云雷也曾说:“非虚构不是一个文体,它应该是一种方法,或者是一种精神,或是一种姿态。我们不是仅仅把它当作一种文体,它是一个与世界重新建立联系的方法。”[28]有学者将“姿态”和“策略”分开论述[29],笔者以为“姿态说”与“策略说”只是描述方法不同而已,并无本质差异。洪治纲在《论非虚构写作》中将非虚构写作定义为“写作姿态”,后又在《论非虚构写作中的主体情感与观念》称非虚构写作为“叙事策略”[30]。
事实上,当下非虚构写作的概念之所以混乱,是由于文体说、文类说和策略说三重说法相互缠绕所致。以上三种说法并不存在对错之分,学者各有自己的研究背景和谱系,所谈虽然都是“非虚构写作”,但具体所指不同。持文体说者主要将“非虚构写作”指向美国的非虚构小说和新新闻报道。持文类说者,如何建明、王晖和丁晓原等人,此前皆为报告文学的写作者或研究者,将报告文学视为非虚构写作或非虚构文学的主要文体也言之有理。而且相对于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作为一种笼统的文类概念,包括报告文学、非虚构小说和传记文学等纪实文体,并无可争论之处。持策略说者主要从当下《人民文学》倡导非虚构写作的特有姿态而言的,这种说法更符合当下非虚构写作潮流发展的具体面貌。三种观点看似矛盾,实际上所谈不在一个层面之上,它们相互补充,彼此共存。
三、非虚构写作的相关概念界定
非虚构写作的兴起给文坛带来新的生机,同时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纪实文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文体、文类和策略三层含义。随着时间推移,由于纪实文学逐渐媚俗,它的文体意识和策略意识逐渐弱化,只变成一种文类的划分方式。当下非虚构写作的概念与纪实文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文体、文类和策略三种说法。因此,厘清非虚构写作及相关概念显得格外重要,否则只会步纪实文学概念的后尘而已。当下非虚构写作及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相关的混乱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与“非虚构写作”自身概念的混乱有直接关系。因此,在探析非虚构写作及相关概念时,首先要对其自身的概念进行辨析,然后从文体、文类和策略三个层面分析,切勿将其混为一谈。
首先,对“非虚构写作”与“非虚构文学”的概念进行界定。目前来看,两者基本处于混用状态,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二者的区别,认为厘清它们的关系迫在眉睫[31]。两个概念同中有异,极易让人迷惑。“非虚构写作”与“非虚构文学”两个概念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前者具有独特的跨界属性和行动属性。“非虚构”后缀“写作”,不仅是名词也是动词,“写作”作动词时,更多了一种“行动”的意思。目前非虚构写作潮流涉及多个学科,“非虚构写作”比“非虚构文学”所指的范围更大。因此,在策略层面,用“非虚构写作”的概念代指这股潮流更为贴切。若“非虚构”以“文学”为后缀,更强调其文学性。在文体和文类层面,使用“非虚构文学”的概念则更加合适。原因有二:其一,文体和文类是文学概念,在文学学科内部谈论文体和文类是题中应有之义;其二,使用“非虚构文学”的概念,可以将其囿于文学学科内部,以避免其泛化。
其次,从文体、文类和策略三个层面,对非虚构写作或非虚构文学与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等相关文体进行界定。
第一,在文体层面,非虚构文学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传入中国,具体是指欧美国家的非虚构小说或新新闻报道。非虚构小说就是纪实小说,这是不争的事实。在2010年之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将报告文学、非虚构小说和传记文学作为纪实文学的三大主要文体。例如,刘建生在《向虚构文学挑战——关于纪实文学的一点思考》一文中说:“传记文学、报告文学、非虚构小说(或称纪实小说,包括历史小说、新新闻写作等)是纪实文学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三个类型。”[32]高文升在《纪实:文学的时代选择——新时期纪实文学研究》一书中认为,“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小说三大板块的形成与稳固,确定了纪实文学体系确立的基本构架”[33]。总而言之,在文体层面,非虚构文学主要指非虚构小说(或称纪实小说),主要指用小说手法写真人真事的文体。
第二,在文类层面,主要厘清纪实文学和非虚构文学的区别[34]。两者无较大区别,都是“nonfiction”概念的两种译法。高晓仙和赵国月在《“非虚构文学”术语翻译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一文中,从翻译学角度对“非虚构文学”的术语进行考察。他们认为:“从翻译学角度看,译名‘非虚构文学’翻译策略属于异化,能体现出属于外来属性,‘纪实文学’翻译策略属于归化,更多地体现出了本土味道。从本质上讲,两种说法都指用同一种非虚构手法创作的文学种类,只是取向和视角不同而已。但作为外来文学概念,凸显其异域特色是首选条件。”[35]两位学者指出,“非虚构文学”和“纪实文学”两个概念是翻译的“取向和视角不同”造成的,但他们认为,应选择“非虚构文学”的概念,以“凸显异域特色”。这种选择造成现在“非虚构文学”概念的混乱局面,文体、文类、策略相互缠绕,非虚构文学、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等概念彼此混用。所以在文类层面,使用“纪实文学”的概念更为合适,原因有二:其一,纪实文学在中国已经发展40多年,作为文类概念,基本取得学界认可,很多大型丛书均使用“纪实文学”的概念,再用“非虚构文学”的概念,新瓶装旧酒,意义不大。其二,从逻辑上讲,非虚构文学相对应于虚构文学,如果将其与散文、小说、戏剧、诗歌四种文体并列,显然于理不通。目前非虚构文学作为“饕餮”,已经“吞并了报告文学”,“挤压了散文”,不少长篇散文也被视为非虚构文学作品[36]。长此以往,非虚构文学的文类秩序会继续混乱下去,弊大于利。因此,建议仍然用“纪实文学”概念代指纪实文类,非虚构小说(纪实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是其最主要的三种文体。
第三,在策略层面上,非虚构写作作为叙事策略,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不存在文体与文类层面的争论。《人民文学》倡导非虚构写作,强调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划清界限,只是为了突出非虚构写作的策略意识,拉近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人民文学》所刊发的非虚构作品除非虚构小说外,还包括人物传记、田野调查、口述实录和长篇散文等文体。这些作品与报告文学相比,更强调个人情感的介入,强调个人的主观真实,也不局限于现实题材,涉及现实、历史和文化三个维度。就文学类型的归属而言,这些非虚构作品和报告文学都属于纪实文学。
总而言之,在文体层面,非虚构文学主要指非虚构小说,与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共同成为纪实文学的主要文体;在文类层面,它与纪实文学无太大差异,建议仍用纪实文学的概念。非虚构文学作为一种文体或文类,由来已久,但用它来代替非虚构小说和纪实文学的概念,只是用新瓶装旧酒,意义并不大,反而使其更加混乱。实际上,2010年后非虚构写作所独有的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策略层面。
四、非虚构写作的策略意识
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纪实文学相比,21世纪非虚构写作的策略意识主要表现在问题意识、行动意识和跨界意识三个方面。
(一)问题意识
21世纪非虚构写作有着很强的问题意识。它的兴起离不开社会的外部环境与文学内部的发展状况。就外部环境而言,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移动互联网持续迭代,现实生活和虚拟网络上出现很多纷繁复杂的“怪现象”,让人难以相信。首先,21世纪以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逐渐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之中。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治理问题、乡村建设问题等。其次,随着电脑、手机等数字科技更新迭代,人类进入读屏时代。一方面,网络世界充斥着大量信息,使人类足不出户便知晓天下大事;另一方面,网络信息杂乱不堪,令人真假难辨,“真实”变得越来越稀缺。
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文学却对现实表达失效。就文学内部而言,非虚构写作有明确的针对性。第一,虚构文学的过度虚构。其一,21世纪初,文学领域出现大量以打工或底层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但由于写作者长期困守书斋,对所写对象缺乏深入了解,导致作品与现实脱节,甚至变为对底层的消费。其二,一些作家自觉远离现实,延续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锋文学的写作姿态,注重对小说形式的探索,缺乏对现实社会的关切。其三,互联网上玄幻、穿越、言情、推理和盗墓等类型小说层出不穷,网络小说作家为吸引读者,构建起一个个或玄妙或扭曲的虚构世界。当中国社会飞速发展时,小说却陷入虚构的泥潭,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失声。第二,以报告文学为主的纪实文学逐渐衰败,失去读者的信任。报告文学作为时代的轻骑兵,本应担负起直面现实的责任,21世纪后逐渐僵化、媚俗化,甚至面临文体衰亡的危机。先是有人声称“恐龙已死”[37],后又有人宣布“是报告文学‘退出历史’的时候了”[38],报告文学在21世纪初陷入困境。正是在文学对现实表达失效时,非虚构写作应运而生。
(二)行动意识
行动意识是非虚构写作最鲜明的口号和旗帜。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提出“深入生活”的口号,倡导作家扎根生活扎根群众,写出无愧于人民的作品。《人民文学》设立“非虚构”专栏后,在2012年第2期《卷首》提出“人民大地,文学无疆”的口号[39],同年第11期《卷首》有言:“本刊自设立‘非虚构’栏目以来,相关作品受到诸多层面读者的热烈反响,‘人民大地,文学无疆’的办刊想象得到了实际体现。诚恳融入现实人生、真切状写世情人心的写作总能引起广泛的共鸣。我们的文学导向经历了从‘二为’、‘双百’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化过程,‘非虚构’文学,也正是对这一导向的响应和践行。”[40]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文艺思想,他说,“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了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要深入生活”[41]。2014年10月31日,邱华栋发表《人民大地,文学无疆》,直接以“人民大地,文学无疆”为题来阐述习近平的讲话精神[42]。可见,《人民文学》倡导的非虚构写作是以往“深入生活”文艺政策的延续,是刊物“人民大地,文学无疆”口号的体现,是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思想的具体实践。
作家、学者等知识分子群体的“行动”也是非虚构写作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在《中国在梁庄》一书中,梁鸿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深知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43]正是对长期封闭的书斋生活产生怀疑,梁鸿返回老家“梁庄”,感受真切的现实生活。她把“梁庄的行走和书写看作一种学术行为”[44],她的“行动”不仅是个人的还乡,也是知识分子主动介入现实的选择。因此,非虚构写作所显示出的鲜明的行动意识,既是《人民文学》贯彻党的文艺政策的一贯主张,也是知识分子主动介入现实的强烈渴望。
(三)跨界意识
跨界意识是《人民文学》设立“非虚构”专栏最直接的动因,也是非虚构写作区别于以往文学现象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人民文学》设立“非虚构”专栏之前,在2010年第1期《留言》已经有所暗示:“我们认为,在这个时代,需要宽阔的、强健的、向着各种艺术形式和纷繁的书写活动开放的文学态度,要收复失地,要开疆扩土”“专业的诗人、专业的小说家、专业的散文家、专业的报告文学家、专业的评论家”不能再“各守一亩三分地”,不能够再“画地为牢”[45]。具体来讲,非虚构写作的跨界意识表现在跨文体、跨媒介和跨学科三个方面。
一是跨文体。十余年来《人民文学》所刊发的非虚构作品包括非虚构小说、田野调查、口述实录、散文、人物传记和诗歌等多种文体。不仅如此,《人民文学》还打破传统的分类方式,在一篇小说中进行跨文体的实践。在《女工记》中,郑小琼同时用诗歌和散文两种体裁表现打工女性的生存面貌。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在散文的叙述中夹杂着大量当事人的口述,还将“梁庄”老支书的顺口溜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二是跨媒介。非虚构写作兴起于文学领域,不少作品首发在文学期刊,再经出版才流入市场。新媒体平台上非虚构写作的蓬勃发展,使非虚构写作真正实现大众化,大量普通人参与进来书写自己的真实故事。更有甚者,一些故事还被翻拍成电影。这种跨媒介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区别于以往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变成当下非虚构写作独有的现象。三是跨学科。非虚构写作不再局限于文学领域,已经成为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最近三年内,学界已经举办多场有关非虚构写作的跨学科论坛。例如,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与《探索与争鸣》杂志先后组织名为“非虚构写作与中国问题:文学与社会学跨学科对话”和“非虚构写作与中国记忆——文学与历史学跨学科对话”的论坛,不同学科的专家在论坛上进行深入对话。总之,当下非虚构写作的跨文体、跨媒介和跨学科的跨界意识,打破了以往文学创作和研究的边界,给文学带来新的生命力,也给其他学科造成不小的冲击。
十余年来,《人民文学》以特有的姿态倡导非虚构写作,真正拉近了文学与现实的距离。但非虚构写作未来走向何处,它的策略意识能持续多久,难免令人担忧。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今天的写作者再也不能忽视当下的现实社会,研究者再也无法忽略纪实文学这一文类的存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的史传传统,20世纪以来纪实文学在中国的兴盛也不是一时的现象,21世纪以来非虚构写作的繁荣也并非昙花一现。也许非虚构写作的策略意识难免有失效的一天,但纪实文学这一文学类型必定会在未来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基金项目:2023年上海师范大学学生科研项目(研究生)“非虚构写作的生态批评——以《人民文学》非虚构作品为中心”(项目编号:23WKY130)阶段性成果]
[1] 何平《非虚构写作和时代思想》,《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8期。
[2] 《人民文学》编辑部《留言》,《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
[3] 参见范以锦、匡骏《新闻领域非虚构写作:新闻文体创新发展的探索》,《新闻大学》2017年第3期;梁鸿《改革开放文学四十年:非虚构文学的兴起及辨析》,《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刘浏《论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命名及其流变》,《当代文坛》2019年第2期;丁晓原《非虚构文学的逻辑与伦理》,《当代文坛》2019年第5期;陈剑晖《“非虚构写作”概念之辨及相关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5期等文章。
[4] “非虚构小说”和“新新闻报道”是记者和作家所采用的不同说法,是文学和新闻领域对同一种写作现象的不同表达,两者虽不完全一样,但也大同小异,都指用小说手法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其中,“New Journalism”也被翻译为“新新闻写作”或“新新闻主义”,与“新新闻报道”基本无异。
[5] 参见董鼎山《美国1978年度最佳畅销书》,《读书》1979年第2期;董鼎山《所谓“非虚构小说”》,《读书》1980年第3期等。
[6] 董鼎山《所谓“非虚构小说”》,《读书》1980年第3期。
[7] 刘茵、理由《话说“非小说”——关于报告文学的通讯》,《鸭绿江》1981年第7期。
[8] 刘亚洲《惊心动魄……女人的名字是“弱者”吗?》,《当代》1983年第3期。
[9] 参见朱寨《关于“报告小说”的求教》,《光明日报》1985年6月6日,第3版;刘茵《为报告小说鼓吹——兼与朱寨同志商榷》,《光明日报》1985年7月4日,第3版;李炳辉《我也谈“报告小说”——兼与刘茵同志商榷》,《光明日报》1985年7月18日,第3版;袁良骏《“报告小说”——一个文学的怪胎》,《光明日报》1985年8月29日,第3版。
[10]俞珑《“纪实文学”创作述评》,《天津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
[11]刘思谦《小说张开了纪实的翅膀——纪实小说审美特性初探》,《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5期。原文中,“Nonfiction Novel”和“New Journalism”被写为“Nonfiction Never”和“New Fournalism”,可能是由于笔误所致。
[12]参见钦键《从“新写实”到“新”纪实——当前小说创作轨迹扫描》,《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彭在钦《世纪末的新纪实小说创作及其策略意识》,《理论与创作》1998年第3期。
[13]杨经建《“新”纪实小说:一种世纪末的创作策略》,《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2期。
[14]文体和文类都是十分复杂的概念。本文所提到的文体皆是文学体裁,文类则是文学类型。简单来说,文体和文类是种与属的关系,文体指具体的文学体裁,文类指某一类文学体裁的总称。
[15]宗原《关于纪实文学》,《世界纪实文学》第1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页。
[16]“非虚构写作”和“非虚构文学”的概念目前基本混用,具体异同在后文会进行详细辨析。
[17]美国的“新新闻报道”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逐渐演变为特稿。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稿在国内开始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成熟的新闻文体。它与非虚构小说并无不同,是文学和新闻领域的不同称呼,都指用文学手法写作真人真事的体裁。当下新媒体平台的非虚构写作由新闻领域的特稿演变而来,相比特稿,也有新的发展。其一,写作者更加大众化,不仅是专业写作者,更多是普通大众;其二,故事题材更为个人化,故事不仅关注社会热点,更多是当事人的真实故事。
[18]梁鸿《改革开放文学四十年:非虚构文学的兴起及辨析》,《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19]范以锦、匡骏《新闻领域非虚构写作:新闻文体创新发展的探索》,《新闻大学》2017年第3期。
[20]参见王晖、南平《对于新时期非虚构文学的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1期;《1977-1986中国非虚构文学描述——非虚构文学批评之二》,《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
[21]王晖《“非虚构”的内涵和意义》,《文艺报》2011年3月21日,第5版。
[22]丁晓原《非虚构文学:时代与文体的“互文”》,《东吴学术》2018年第5期。
[23]何建明《创意写作理念与实践:中国非虚构文学的新契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24]陈竞《李敬泽:文学的求真与行动》,《文学报》2010年12月9日,第3版。
[25]邱华栋《“非虚构文学”这个筐》,《深圳特区报》2011年12月6日,第B06版。
[26]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27]张文东《“非虚构”写作:新的文学可能性?——从〈人民文学〉的“非虚构”说起》,《文艺争鸣》2011年第3期。
[28]李洱、梁鸿、李云雷等《非虚构与虚构(上)》,《上海文学》2012年第3期。
[29]参见刘浏《“非虚构”的十年讨论与中国非虚构文学研究》,《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
[30]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中的主体情感与观念》,《文学评论》2022年第5期。
[31]参见冯骥才《非虚构写作与非虚构文学》,《当代文坛》2019年第2期;袁凌《“非虚构文学”亟需面世》,《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4期。
[32]刘建生《向虚构文学挑战——关于纪实文学的一点思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33]高文升《纪实:文学的时代选择——新时期纪实文学研究》,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34]此前也有学者提出过“大报告文学”的概念,但影响不大,参见李朝全《报告文学的范畴泛化及创作底线》,《南方文坛》2012年第1期;李朝全《“大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文体探析》,《文艺报》2012年5月4日,第2版。
[35]高晓仙、赵国月《“非虚构文学”术语翻译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外国语文研究》2017年第5期。
[36]金理《当“非虚构”变成饕餮,“文学”还能提供什么》,《南方文坛》2021年第4期。
[37]李敬泽《报告文学的枯竭和文坛的“青春崇拜”》,《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文化版。
[38]黄浩、黄凡中《报告文学:文体的时代尴尬——对报告文学“生存艰难”的本体质疑》,《北方论丛》2009年第1期。
[39]《人民文学》编辑部《卷首》,《人民文学》2012年第2期。
[40]《人民文学》编辑部《卷首》,《人民文学》2012年第11期。
[4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42]邱华栋《人民大地,文学无疆》,《文艺报》2014年10月31日,第2版。
[43]梁鸿《中国在梁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44]梁鸿《书斋与行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0期。
[45]《人民文学》编辑部《留言》,《人民文学》2010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