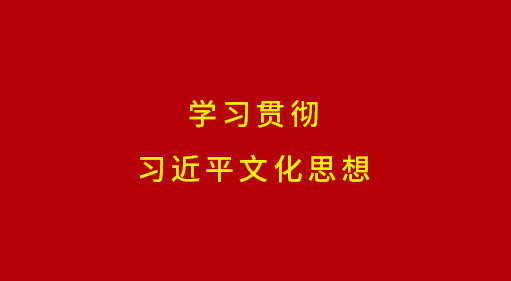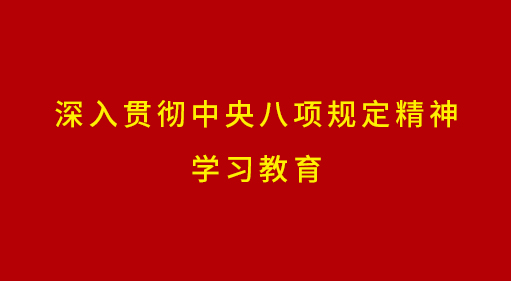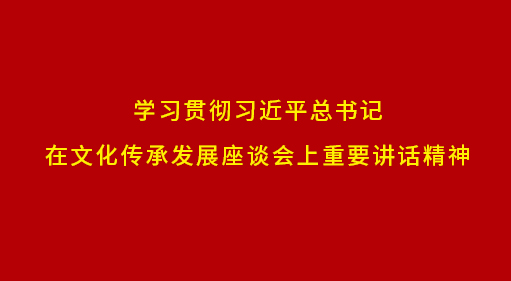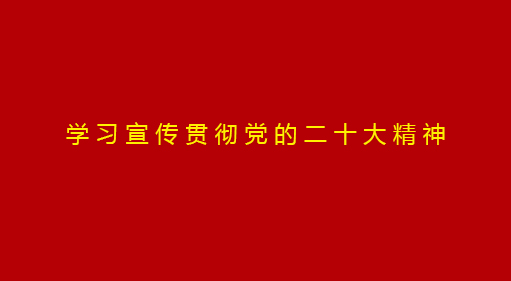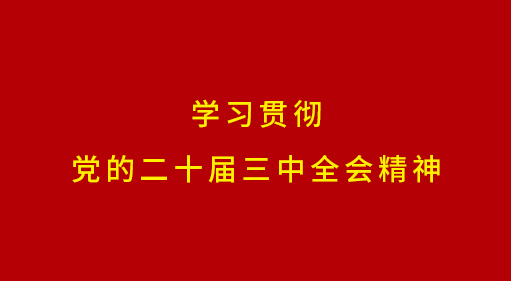神经美学视阈下的中国意象审美三阶段说
时间:2023-09-04
胡 俊
摘 要:西方神经美学研究在大量的实验实证基础上提出审美过程的动态神经机制模型,这些模型研究建立在西方审美思维的基础之上,对于中国本土审美脑机制的研究,虽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缺乏中国审美思维的本土特色和独特文化规律。结合中国意象审美的丰厚资源来进行中国本土神经美学研究,建构出中国意象审美的脑机制模型,提出符合中国人脑审美欣赏和创造运行机制的审美过程的三阶段说,从而创新和充实中国神经美学研究的具体路径,同时也从新的研究角度来丰富中国意象论美学的研究。
关键词:神经美学;审美三阶段模型;意象审美
根植于实验美学,探索大脑审美神经机制的新兴学科“神经美学”,源于1999年英国伦敦大学泽基(Semir Zeki)教授的首创,主要是通过脑科学的实证成果来探究审美客体的特质、审美相关脑区结构和功能、审美活动的脑神经加工机制等,形成一种新的美学研究路径。20多年来,国外关于神经美学的研究已成规模,目前英、美、德、加等国已有数百位神经美学家,成立的专门研究机构或协会有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神经美学研究所”、德国莱比锡大学“神经美学协会”等数十家。国内目前翻译介绍和阐释神经美学的著作、论文已逐渐增,然而缺乏美学理论的深度挖掘,再加上使用很多神经科学的术语,使得很多美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对于神经美学虽觉新奇,但学科壁垒导致难以深入研究,尤其是对于脑审美机制的研究,不仅国外神经美学家们阐释得不够清楚,而且国内研究虽紧跟国外步伐,但仍缺乏中国独特的研究路径和思想创见,因此,我们倡议中国学者借助中国美学的思维方式和智慧成果,来融合创新性地阐释和研究神经美学。
中国古代的审美意象理论是博大精深而富有智慧的,值得今人继续深入探究。我们在这里试图运用中国美学的思想和智慧,尤其是古代审美“意象”思维模式,并结合西方神经美学的研究成果,来重新划定审美脑区及运行机制,创新性阐述审美欣赏与意象创构的脑机制,希望拓深已有神经美学理论,同时建构中国神经美学的核心范畴和基本理论框架体系。
一、西方神经美学的审美脑机制模型研究
神经美学研究的开始阶段,西方神经美学家们主要是运用脑影像技术,研究了不同审美材料及审美活动分别激活了被试者大脑的哪些脑区,并研究了这些激活的脑区在审美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并对审美相关的这些脑区进行定位和功能细分。在掌握了相关脑区在审美中的功能定位和结构关联的基础上,后来的神经美学研究更加关注人脑审美活动的运行机制,包括人脑审美感知、情感、判断等复杂动态的整体加工过程。神经美学家们依据不断积累的脑成像实验成果,对审美活动过程中人脑神经的运行机制进行了阶段划分,建构了人脑审美活动过程的几种神经机制加工模型,对人脑处理审美过程进行了科学假设和严谨推测,对之后的神经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查特杰的视觉审美三阶段模型及审美三环路
在神经美学史上,2004年查特杰首次提出人脑神经视觉审美机制的“三阶段”模型[1],该模型把视觉审美神经加工过程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早期加工阶段主要是由枕叶皮层对形状、颜色等物体的视觉属性因素进行提取、分析,主要体现在视觉专化区的激活;中期加工阶段主要是通过颞叶区对已提取的视觉信息进行筛选和加工,激活相关记忆信息来赋予审美对象一定意义,主要体现在大脑海马区的激活;晚期加工阶段主要是眶额部皮层和尾状核会激活、引发主体的审美情感反应,前扣带回和背外侧前额叶区被激活,主体产生审美偏好,产生审美情感,做出审美判断。
2014 年,查特杰和瓦塔尼安提出审美三环路的加工模型[2],并在 2016 年对审美三环路展开了具体论述[3],包括三环路的具体脑区、运行机制和相关作用等。这一审美神经加工模型是在 2003 年查特杰审美体验三阶段说的基础上,依据审美活动三个阶段的不同脑区神经活动的结构和功能提出的。根据查特杰审美三环路的模型,审美体验是由下面三个神经系统共同引发的心理状态,虽然三个神经系统不一定对审美体验有着同等的意义。一是依据审美活动激活了枕叶、梭状回、内侧颞叶、运动系统乃至镜像神经元系统等,提出人脑审美的“感觉—运动”神经回路,主要负责对审美对象基本特征进行感觉、知觉加工和具身认知的。二是依据审美活动激活了眶额皮层、内侧额叶皮质、 腹侧纹状体、前扣带回和脑岛等,提出“情绪—效价”神经回路,主要负责个体审美过程中审美情绪、奖赏、喜爱等状态的神经环路。三是依据审美活动激活了内侧眶额皮层、腹内侧前额叶等,提出“知识—意义”神经回路,主要负责专业知识、语义背景和文化有关功能等。“我们能够从艺术品的感官品质之外提取出其语义属性的程度,会影响到神经系统为审美体验服务的参与程度。”[4]也就是说,在审美过程中,以意义和知识为形式的自上而下的加工对审美体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使得我们对艺术的体验受到其感性品质之外的因素的影响,涉及处理艺术的语境和语义等,最容易受到个人、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是形成个性化的审美体验的最重要一环,也是目前人们了解最少、也是最值得研究的。
(二)莱德等的审美体验五阶段模型
2004 年莱德等提出审美体验五阶段加工模型[5],经常被神经美学家们引用作为相关理论的基本发展框架。该模型与查特杰的三阶段说相比,把审美过程设想得更为具体,包括“感性分析”“暗示的记忆整合”“明确的分类”“认知掌握”“评估”等神经认知加工回路。认知信息流在这个模式的某些部分是单向的,而在其他一些部分又是双向的。输入这个神经回路系统的是艺术品本身(主要限于视觉刺激物),在每个阶段,一个特别的运作将执行在视觉刺激物上,从而提取视觉刺激物的不同特征。因此,在已经提取了视觉刺激物的感性属性之后,会把它放置进一个自我参考的(暗示的记忆整合)和明确的(明确的分类)环境中,在认知掌握期间评估放置在艺术品上的意义和阐释。如果认知掌握是成功的,而且主体成功地阐释了这一艺术品,这一艺术品会被评估为好的或坏的艺术作品。那些审美判断将会分别地伴随着积极或消极的审美情感,另一方面,如果认知掌握是不成功的,而且主体失败于解释这一艺术品,那么它可能会被评估为坏的艺术作品,伴随着消极的审美情感。也就是说,最后通过认知状态的理解或模糊以及感情状态的是否满足,产生审美判断和审美情感的输出。
因为莱德的审美体验模型受到广泛的关注,十年后,莱德和纳达尔(Marcos Nadal)还对该模型进行了完善和修整,之前莱德认为审美过程中认知加工和感情加工可能是分开的,不一定有正相关性,后来莱德等认为审美过程中认知和感情加工是不断相互作用的,因此在上述认知信息流之外,还增加了一个平行运行又不断交汇的人脑审美的“感情评估流”[6]。莱德等后来认为审美加工是由审美认知流和审美感情加工流构成,认知加工五个阶段的输出结果不断调节和修正情感状态,同时情感状态又对认知加工进行相关渲染和引导。
(三)侯夫和雅各布森的审美生产三阶段模型及其他
侯夫(Lea Höfel )和雅格布森(Thomas Jacobsen)研究了音乐、诗歌、绘画和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2007年提出审美生产过程的三阶段说[7]。该模型认为审美过程包括审美感受、中央处理和审美产出三个神经加工阶段。“第一阶段是感受阶段,主要是与知觉加工有关的枕叶、颞叶皮层区的脑区神经被激活,对审美客体进行知觉加工。第二阶段是中央处理阶段,主要是由与工作记忆、情感反应和认知控制有关的前额叶皮层、扣带回等脑区神经完成对客体审美价值的思考,做出审美判断。第三阶段是产出阶段,主要是由控制身体动作的运动皮层负责,作出外显行为,进行绘画、音乐、诗歌和舞蹈等方式的审美表达”[8]。
此外,在综合比较查特杰和莱德的两个审美加工模型基础上,2007年瓦塔尼安和纳达尔提出审美体验的模式组合,认为艺术体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物体和感知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认知和情感过程的相互作用。
卡普切克(Gerald C. Cupchik)及其同事试图通过研究认知控制和知觉促进对审美体验的贡献来理清审美欣赏中涉及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路径[9]。受试者观赏了各种具象绘画作品,包括强调轮廓和构图的线性硬边风格绘画作品,以及开放式软边表现风格的绘画作品。受试者们被要求从实用主义和审美角度进行观赏。具体而言,在实用情景下,他们注重获取有关绘画内容的信息,而在审美情景下,他们则注重体验绘画的意境,并且欣赏绘画带来的感觉。基线刺激物包括抽象绘画作品,这种作品只要求受试者进行观赏。研究结果表明,与从实用角度观赏硬边绘画相比,当受试者从审美角度观赏软边绘画时,左侧顶上小叶的活性得到增强。实验者将这种自下而上的激活归因于观赏者试图分辨软边绘画中的模糊外形,以便在审美情景下构建连贯图像。这与先前关于顶叶在空间认知和视觉意象中的作用的研究结果一致[10]。审美刺激物和基线刺激物之间的对比显示双侧脑岛被激活。如上所述,这种激活因情感体验诱发,这与迪奥及其同事[11]以及汉森及其同事[12]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在实用主义观赏情景中,因为对有意义的对象进行了识别,并且将情景模型施加于图像场景,所以激活了右侧梭状回。此外,左侧前额叶皮质参与了自上而下的内部自我参照目标控制,这些目标涉及由审美情景规定的审美感知。总之,这项研究表明审美体验来源于自上而下的注意力定向(前额叶皮质)和自下而上的知觉输入之间的相互作用[13]。
依据神经美学脑成像实验成果,审美过程中不仅有人脑认知的跨知觉分析,也有情感的连接,还有关联的想象,以及判断的推理,乃至意义的校准,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神经通路。也就是说,审美神经的加工过程包括审美认知、审美情感体验、审美判断、奖赏等。
总之,以上这些审美机制模型偏重于西方认知心理学的学科背景,从审美过程中认知和情感因素的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以西方审美脑实验中的实证成果为支撑,来建构和推测审美神经运行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但从中国意象审美思维来看,审美过程不仅是一般地涉及认知和情感,审美还具有自身的独特的方式和规律,这离不开审美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即审美意象的生成,所以我们将在下文结合中国意象理论,建构中国意象审美的人脑审美机制三阶段模型。
二、建构中国意象审美的三阶段模型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观”“品”“悟”能够形象表达对审美对象进行审美欣赏的动态过程。“观”是指欣赏者通过“观物取象”来感受该事物或艺术作品。“品”是指欣赏者根据自身的文化、社会背景和个人经历形成的审美心理经验和文化结构来凝神静听,并关联主体的记忆和想象,在品味作品过程中使之得以丰富,并使得意象呼之欲出,一旦意象产生,标志着进入“悟”的阶段。“悟”就是欣赏者在对意象再加工并发展到审美意象,最后升华出一种意境的领悟或悟道。
审美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初级感知加工阶段,可以借助中国古代美学中的“观”来理解。人脑审美过程的第一阶段,通过“观物”来“取象”,即审美材料的客观刺激信息通过眼睛、耳朵等感官的捕捉和搜集,然后把光信号、声音信号传导到视网膜、耳膜,然后转化为神经信号中间经丘脑筛选,传输到大脑枕叶、颞叶等视觉、听觉皮层,经过对审美客体的初步感觉属性的加工和编码,同时神经镜像元系统再利用这些属性加工信息,通过类似镜像、刻录的功能对物理真实世界中的物体、人物、事情进行初级客体属性编码,储存在大脑中,即在脑中产生了“象”,可谓脑中之象,越是美的等级高的客体,越是会在大脑中产生栩栩如生的象。在审美过程中,一旦形成栩栩如生的“象”,就开始进入审美欣赏的下一个阶段,即对“象”的仔细品味。
审美过程的第二阶段是高级认知和情感加工阶段,可以用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品”、“味”来理解。人脑审美欣赏过程的第二阶段,通过“澄怀味象”,人对脑海中物体之象的神情气韵进行细细品味、揣摩,其脑神经机制实际上是在进行审美高级认知加工和情感加工的双向并行处理过程,审美过程中人脑的高级认知加工流包括感知分析、内隐记忆整合、联想及想象、明确分类、认知掌握、意义附加、认知评估等步骤。伴随着认知加工流,人脑中同时还有与其平行运行并可交流交互的情感评估加工流。在这一阶段认知和情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双核处理的加工结果是会在脑海中在“象”的基础上形成基本的意象,产生对该事物或美或丑或中性的审美判断,这就开启和进入了人脑审美过程的第三阶段,即“妙悟”“悟道”的阶段。
判断为美的审美对象,还会同时带来审美愉悦奖赏。如果是一般吸引力的审美对象,产生一般的审美判断和审美愉悦,也即意味着审美过程的结果或结束。但如果是具备审美吸引力的审美对象,那么产生初步的审美判断和审美愉悦,还只是处于审美第三阶段的早期,在审美第三阶段的中期还会吸引大脑打开默认系统即心智系统,开启沉浸体验式的对于美的初步“意象”的审美深度加工阶段,是以审美意象的追寻和捕获为核心,并伴随着深度审美愉悦。一旦形成比较完满的典型的审美意象,就意味着进入审美第三阶段的后期,我们会伴随着审美高峰体验,在悟道中甚至达到至美的审美意境。所以说审美第三阶段是高级审美活动的核心阶段,是大脑高创造力的审美活动,并一直伴随着强烈的审美愉悦体验。
客体的相关感知觉信息进入大脑以后,经过第一阶段的视听觉信息初步处理,形成了象,再通过第二阶段高级认知和情感的共同表征加工之后,形成了初步的意象元素,逐步在大脑中生成和创构出意象。经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两个层面的感官感知、高级认知和情感加工后,产生了审美判断,大脑会初步判断出刺激材料的“意象”为“美的”“丑的”或“中性的”,并且判断为“美”的刺激物还同时激发审美愉悦奖赏,这也意味着已进入第三层面的综合融会加工,即判断结果为“美”也就意味着进入在审美过程的第三阶段。判断为“美”的刺激物,特别是判断为最打动人心的“美”的刺激物会继续激发人脑进行“审美意象”的生成和创构,以默认网络为首的脑区激活,对大脑中的美的审美对象的意象表征,进行具身化和心智化再加工,同时连接第二阶段已经激活的大脑有关意义、记忆、共情和奖赏系统等,促使审美意象的生成和创构。
我们借助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从“虚静”到“神与物游”,再到生成“审美意象”,来理解审美欣赏过程中审美意象生成和创造的脑加工机制。“虚静”是审美意象追寻、生成和创造之前的人脑准备阶段,这时人脑需要准备进入一种静息状态;然后大脑进入“神与物游”的状态,即人脑对于审美意象的捕捉和追寻。人脑在记忆、想象、情感、语义等功能脑区高度激活,并联结启动了人脑的默认网络的激活,它们同时高度激活和互动加工;使用生成“意象”来表明审美意象创构的开始,然后对“意象”进行审美再加工,欣赏者大脑中想象、创造出的意象一旦生成,也同时再成为审美加工对象,所以大脑中的社会心智推理和自我反思区联合第二阶段已激活的高级认知加工区和情感加工区,依旧会对创构出的意象再度加工,这样最后完成“审美意象”的创构和鉴赏。接着乃至从“审美意象”发展到“审美意境”,最终构造成一个独立的完满的审美世界,可以带来持续共振的审美愉悦,但也带来在保持基本核心内涵下的仁者见仁的差异化个体美感体验。
从神经美学角度具体阐释审美意象生成和创构的动态脑区结构及脑神经机制问题,揭开了千年来中国审美意象理论的大脑运行过程的神秘面纱。同时借助中国美学“意象”理论中的丰富思想资源,也有益于比较生动自然、妙趣横生、茅塞顿开地揭示神经科学领域中抽象复杂的审美大脑机制研究,也是对当前神经美学实验中侧重研究脑区激活的意义提升,使得我们能从神经美学实验数据中发掘出更多的美学理论建构价值。
三、启示和意义
进行神经美学研究,不仅要掌握已有神经美学的实证成果,把实证成果与美学基本问题进行融通,从而在脑神经机制的新视角下来研究当前中国美学发展中仍然还待解答的一些问题,而且还需以“意象”为首,运用中国审美智慧和思维,融合已有神经美学成果来熔铸和创新美学基本理论。一方面,可以借助神经美学实验中的实证成果来阐释中国意象理论,会在当前中国意象理论研究深厚积淀的基础上,从崭新的研究路径来回应意象论美学中的核心理论问题,比如美与意象、意象与审美意象的关系等,可以从脑审美机制角度给予比较科学实证的甄别和阐释。另一方面,中国意象理论经过从古至今几千年来中国学人的实践和加工,已趋于完美,这也是全人类的智慧结晶,其丰富的思想资源应该具有普适性,尤其是当前的意象论美学更具有现代价值,意象创构理论能为当前的神经美学研究起到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推进神经美学的纵深研究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从而建构中国意象神经美学学科体系。具体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借助中国意象美学思想来理解和阐释神经美学成果。从当代现有美学知识的角度很难理解神经美学的专业知识及术语、表达和思路,所以可以借用中国美学中的“意象”“意境”来理解“神经美学之父”泽基提出的“人脑-艺术契合论”中的“情境恒定性”,再如用“虚静”“神游”来理解审美欣赏和文艺创造中人脑默认网络的结构、功能和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可以结合意象论美学中的思想,比如“意象的创构以感性对象的价值特点为基础,经历了‘感知—动情判断—创构’的过程”[14],来理解和阐述美感高峰体验状态的脑神经机制,当然我们也对此进行了完善、补充、丰富和修正。我们提出在人脑经过对审美对象材料的初级感知、高级认知和情感加工阶段以后,就有可能作出审美判断,并激发大脑奖赏机制,开始产生愉悦反应,人脑会逐步形成了一个有着形象组合、充盈着情感和蕴含着意义的意象,人脑中一旦捕获或生成意象,会对意象进一步加工,乃至继续创构具有“象、情、意”高度完满性的审美意象,会激发大脑审美高峰体验,并持续对审美意象进行再加工,最后达到妙不可言的审美意境,让人们久久被大脑中建造的美妙绝伦的完美艺术世界所萦绕。这样通过研究脑审美机制,我们会发现意象创构不仅有初级感知加工,还应该有想象、推理、评估以及意义赋予等高级认知加工;而且意象的创构和生成不是审美活动的结束,而是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脑神经接着还会对意象进行加工和完善,最具有吸引力的意象会刺激大脑进行更深层的审美体验,进而产生审美意象,乃至达到审美意境。
二是运用中国意象美学思维和智慧来进行神经美学的理论建构。我们运用“意象”等中国美学范畴和美学思维,对审美活动过程进行深度神经美学阐释,比如借鉴“观”“品”“悟”的意象追寻,来推测中国神经美学研究意义上的审美欣赏脑神经机制;借助“虚静”“神游”“审美意象”,来理解中国神经美学研究意义上的审美意象创构脑神经机制。另外我们还借助中国审美中的“言象意”范畴,来研究神经美学中重要一环——审美客体,提出中国神经美学研究中的客体审美特质范畴[15]。运用中国审美“意象”思维与神经美学成果进行对接,首次设计审美神经加工的中国美学路径,提出意象审美过程的人脑动态加工机制的中国神经美学模型。
三是借助中国美学的智慧来思考和解决神经美学中悬而未决的问题。神经美学的发展一直沿用西方神经科学的思维和研究方法,这也产生了学科局限和发展困境,尤其是内部出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人脑审美思维神经网络变化过程,对此,我们试图运用中国美学中“意象”“言、象、境”等含有很多质朴而精深的中国美学智慧和哲学思想,来破解当今神经美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度融合创新思考。一是针对美学史乃至神经美学史上,关于审美主要是一种认识过程还是一种情感体验的观点分歧,提出审美过程中的认知和情感的双螺旋平行加工机制,有幸在当下的“意象创构论”中得以感到共鸣,比如“意象创构论”提出“情与理统一于意,情理交融是意的核心”,“‘意’中包含着丰富的情感和理智的统一”。当然,笔者虽然非常认同审美活动中情与理的统一,但是观点还是有细微的差异,比如朱志荣在“意象创构论”中认为“情是理的基础,情感的感发是意的基础”,“‘意’中包含着的情理关系,乃是以理节情”。笔者认为大脑的认知加工回路和情感加工回路是两条不同的线路,它们是并行处理刺激材料的,但两个神经回路之间也是相互有神经连接点的,可以在加工过程中相互影响。因为情感和认知是两条神经加工路径,虽然情感会影响到认知,但并不形成“理”或“意”的基础,因为“理”“意”作为一种推理和意义赋予的高级认知加工,它的基础主要是对于刺激材料的初级感知加工的结果。二是针对人脑是否有独特审美区,提出审美脑区是一般通用脑区和核心审美脑区的结合,并提出动态的审美意象加工机制。我们认为审美过程是由多个功能脑区完成,审美过程的前中期征用了大量共用的一般感知、认知和情感脑区,只有在中后期,当人脑通过复杂的内容、意义的认知评估和情感深化加工之后,初步形成意象,经过深度审美体验,核心审美脑区被强烈激活,大脑中形成审美意象,乃至进入审美意境的体悟状态。
神经美学视阈下审美意象的创构和鉴赏研究不仅具有以上理论意义,它还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其一,系统剖析和阐释人脑审美活动的脑区结构、功能和机制,有助于人们科学理解审美欣赏和审美创造过程中的脑部活动,尤其是审美体验中意象的生成,进而揭开人类审美的心脑奥秘。其二,人脑审美意象机制涉及人类基本感知、高级认知、记忆、学习、情感、决策等多种脑区及神经网络,本研究不仅为人类用审美欣赏和文艺创造活动,提高认知功能、提升心灵修养、净化社会环境等找到科学依据和途径,还可用于审美医学等领域,进行人脑认知和情感功能的治疗和康复。其三,构建中国审美“意象”思维的人类审美脑谱图和神经机制,有助于将来研发和生产具有中国人审美品位和审美思维的人工智能审美机器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美学视阈下的脑审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BZW028)阶段性成果]
[1] Anjan Chatterjee. “Prospects for a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Visual Aesthetics. ” Bulletin of Psychology and the Arts 2(2004):55-60.
[2] Anjan Chatterjee and Oshin Vartanian. “Neuroaesthetic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8(2014):370-375.
[3][4]Anjan Chatterjee and Oshin Vartanian.“Neuroscience of Aesthetics.”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369(2016):172-194.
[5] Helmut Leder, Benno Belke, Andries Oeberst and Dorothee Augustin. “A Model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Aesthetic Judgment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4(2004):489-508.
[6] Helmut Leder and Marcos Nadal. “Ten Years of a Model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Aesthetic Judgments:The Aesthetic Episode Developments and Challenges in Empirical Aesthetic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5(2014):443-464.
[7] Lea Höfel and Thomas Jacobsen. “Electrophysiological Indices of Processing Aesthetics, Spontaneous or Intentional Proces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1(2007):20-31.
[8] 胡俊《艺术·人脑·审美——当代西方神经美学的研究进展、意义和愿景》,《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
[9] Gerald C. Cupchik, Oshin Vartanian,Adrian.Crawley & David J.Mikulis. “Viewing Artworks:Contributions of Cognitive Control and Perceptual Facilitation to Aesthetic Experience.”Brain and Cognition 1(2009):84-91.
[10]Scott L. Fairhall & Alumit Ishai. “Neural Correlates of Object Indeterminacy in Act Compositions.”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3 (2008): 923-932.
[11]Cinzia Di Dio & Vittotio Gallese. “The Golden Beauty:Brain Response to Classical and Renaissance Sculptures.” Plos One 11(2007):1201.
[12]Peter Hansen,Mick Brammer & Gemma A.Calvert. “Visual Preference for Art Images Discriminated with FMRI.” Neurolmage 5(2000):739.
[13]Gerald.C.Cupchik,Oshin Vartanian,Adrian.Crawley & David J.Mikulis.“Viewing Artworks:Contributions of Cognitive Control and Perceptual Facilitation to Aesthetic Experience.” Brain and Cognition.1(2009):84-91.
[14]朱志荣《论审美意象的创构》,《学术月刊》2014年第5期。
[15]胡俊《神经美学与审美意象理论的创构》,《文学评论》2022年第5期。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