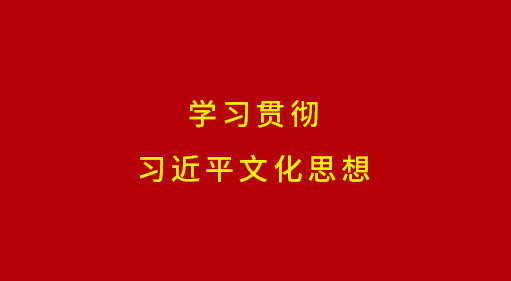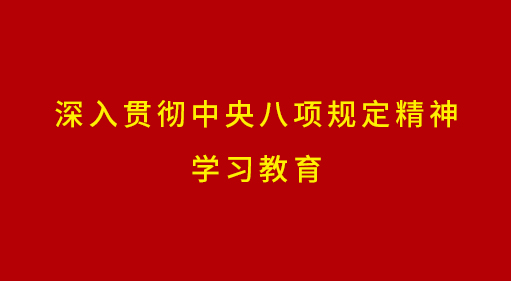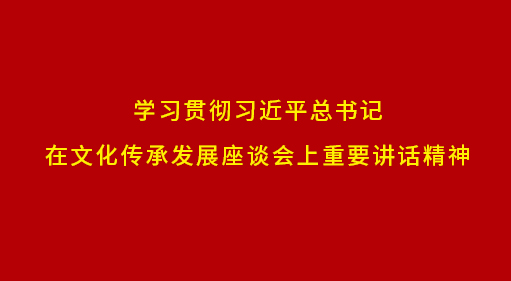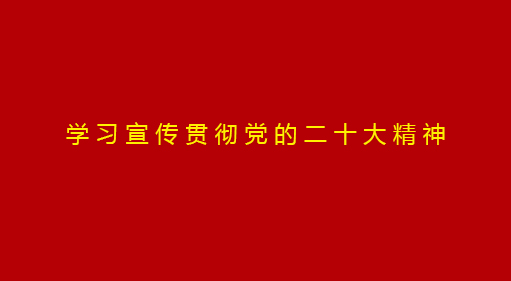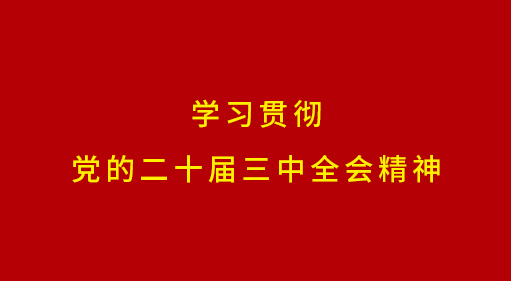观听与歌唱:原型批评与中华文化意象空间的建构——以傅道彬《晚唐钟声》的意象分析 为中心
时间:2023-07-07
田恩铭
摘 要:原型批评是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傅道彬通过对中国文学原型批评的全面考察,从中发掘出中国文学的审美价值。在中体西用理念下拈出原型,摄取兴象,捕捉自远古而来的歌声,进一步发掘中华文化的审美价值。诗性意象、自然意象、文化意象构成作者阐发诗意的意象空间,形成一次意象史意义上的美的巡礼。研究中华文化就要以所摄取的自然意象和文明意象建构中华民族早期文化的精神家园,创造性地提供解读中国文学经典的原型批评方法。面对一部充满诗性智慧的可读性文本,研究者以《周易》《诗经》建构了中国文化的形象系统,从而揭示出中华文化的诗性智慧。学术界只有不断地发掘中华古典时代的文学传统,才能还原中华民族动人心魄的审美历史。
关键词:原型批评;文化意象;文学研究;傅道彬
如果考察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著作的影响力,《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下简称《晚唐钟声》)一定是不可或缺的。《晚唐钟声》是傅道彬早年的学术著作,是一部充满诗性智慧的可读性文本。这部著作之所以堪称经典,就在于它以中体西用的研究理念引入原型文化,在中国诗学与原型批评的碰撞中回应了当下依然重要的学术命题:如何阐释隐藏于风雨江山中的中华文明史。
当我们静下心来谛听自然的回响,祖先的思想熠熠发光。对于文化传承的追源溯流让我们在绚烂星空中聆听远古的呼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文化基因化作文化记忆的图景通过甲骨文、石刻、抄本、写本最终到印刷出版,如同缕缕青烟绵延不绝。如何追踪历史的陈迹进而去探寻诗性的光亮?当原型批评被纳入研究视野,将诗学意象与之结合,用心观听自然意象和文化意象,远古的歌声便具有了现代价值。就此而言,《晚唐钟声》为我们提供了追寻的路径,沿此前往会走进意象世界,探寻华夏祖先所营构的心灵家园。
一、诗学意象与文化原型
原型批评是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以原型批评融入文学意象之中,《晚唐钟声》乃是一部以诗意的语言阐释中国文学经典的著作,著者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出发,沿着文学主题的原型意象一路寻踪追迹。从弗洛伊德到荣格、弗莱,文化原型批评逐渐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西学东来的20世纪90年代,寻根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共同母题,《晚唐钟声》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原型批评走进精神的领地,犹如考古学家走进发掘的田野,只不过考古学家寻找的是文物是遗迹,而原型批评寻找的是形式是语词,如同物质文明的碎片有案可稽一样,原型也是可经验可凭借可证实的实体。”[1] 原型批评与中华诗性智慧相遇,自然就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会找到追根溯源的切入点,提出新的问题进而展开探寻的历程。
研究汉语文学的宗旨是什么?叶舒宪认为:“从古汉语的早期文字使用中,寻觅来自口传文化和宗教神话观念的关键词,据此分析和还原神圣言语活动在古人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给在后代书写文明中被遮蔽和遗忘已久的‘文学发生’问题,开辟一种知识社会学的重新理解之途径。”[2]引出话题之后,《晚唐钟声》的第一章“兴与象:关于原型的古老诠释”具有概述性质,可分为两个部分:原型与中国文化的兴象,兴象系统与文化密码的破译。原型与中国文化的兴象是如何建立联系的?源自历史内蕴的丰富性和文化传统的可继承性。该章的第一节中,著者认为“原型”是一部凝缩了的人类文化史,“原型总是自发地显现在神话、童话、民间故事、宗教冥想、艺术想象、精神幻想的状态中”[3]。原型的第一个特征在于是从悠远的历史出发的,因此“人类不仅仅在血缘上继承着祖先的生命,而且在文化上也继承着祖先的传统和历史”。我们阅读祖先留下的只言片语可能就触摸到传统和历史。第二个特征是象征表现形式。只有找到原型,由此出发才会找到历史文化的转化形式。第三个特征是原型负载着无意识内容。弄懂集体无意识的涵义才能读懂原型,“由于原型缩短了现代与远古社会的距离,找到了我们同远古历史与文化的联系,这对于现代人那些无家可归的灵魂,是莫大的慰藉”[4]。原型批评非神话学所能限制,一经诞生便迅速闯入语言学、民俗学、文学、艺术学等研究领域中去了。原型研究的意义何在?在傅道彬看来,就在于“帮助人们认识并返回自己灵魂的故乡”。这常常让我们想起王安忆、阿城、韩少功的寻根小说,源于祖先的灵感迸发可能会发生拯救意义。紧接着回到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历史现场,拈出“兴”和“象”,建构了中国文化的原型系统。著者先是阐发古代典籍中关于“兴”“象”的解释,而后引入西方原型理论。“兴与象已构成了中国上古文化的原型系统,兴象正是依据简洁的形式概括最丰富生动的上古人类文化史”[5]。为何下这样的论断呢?作者认为:兴象根源于远古文化的传统,某些意象在《诗经》《易经》之中具有文化传统所赋予的象征意味;兴象是深刻的象征,著者以《诗经》“白茅”意象为例分析所蕴含的女性象征意味;兴象与无意味有关联性,一旦形成集体无意识便带来意味的丧失。
诗学意象是在文学长河中凝练出特有的表现手法。兴与象是中国诗学的核心意象。傅道彬以中体西用为研究理念抓住兴象系统就为以原点为中心破译文化密码提供了一个支撑点,由此出发去还原隐于其中的文化谱系。《晚唐钟声》以《周易》《诗经》建构了中国文化的形象系统,通过上下求索从中发掘出“充满一片蛮荒的自然的生命情趣”。以发现的眼光提出学术问题,如以《易经》的“咸卦”、《诗经》的《周南》《召南》为例还原了“中国文化还呈现出一片生命盎然的世界”。当我们走进上古的兴象世界,如何破译文化密码呢?著者拈出“云与雨”“山与泽”“猪与淫欲”“水—礼的象征意义”这样四个意象范畴以破解各自的文化原型意义。经过一段探寻的历程,作者认为:“兴与象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文化原型,它反映着上古文化的隐喻系统,也反映着与这个隐喻系统息息相关的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6]论断一出,就为我们揭示了阅读的意义所在:只要找到古老的文化原型就能够循此前行,发掘文学史中存在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二、自然意象与文化原型
兴象系统无疑是在自然的体验中找到并加以诠释而成。从上古文明到大唐风度,历史的跨度不可谓不大,文化的转型不可谓不迅疾,然而所蕴含的原型意义依然相当一致。傅道彬选取了月亮、黄昏、森林、雨等四个自然意象进行文化考古和诗意诠释,为我们敞开了通向传统的文化之径。
月亮、黄昏是自然意象中的两个不同概念,月亮是夜的魂魄,而黄昏是夜晚来临的前景。《中国的月亮及其艺术的象征》是一篇结构严谨而诗意融融的大文章。月亮没有国界,月光没有固定的界域,而中华文化孕育了中国的月亮。第一节“月亮与女性和母亲世界的原型”追溯月亮与女性世界的温馨与忧伤,从女娲补天到嫦娥奔月,月亮有了基本的象征意义,其一是“月亮是母亲与女性的化身,反映女性崇拜的生命意味,代表母系社会的静谧与和谐,她反映着女性世界的失意与忧伤。”同时月亮具有永恒的象征。作者进一步探寻衍生义,象征美、象征孤独与失意,“象征着和谐静谧中的中国智慧和超群拔俗潇洒诗意的士大夫风范”[7]。第二节“月亮本体与中国哲学及智慧的象征”主要探寻月亮与时间的关系,涵括对永恒存在的神秘思索,这种思索离不开心灵的超脱和愉悦;包含澄明宁静、澡雪精神的心灵体验;对人生意趣的活参顿悟,如作者所说:“月亮像一个无言的哲学大师,引导人们对超越、空灵、神秘的智慧品格的思考。”第三节“月亮原型与古典审美意境的创造”回到文学审美层面,通过诗句意象化找到月亮意象使用的规律,一是“月亮意象的出现总伴随着阔大苍凉的宇宙空间、浩渺悲壮的天问意识和雄浑高古的审美境界。”二是“月亮创造了心灵虚静和空间澄净的审美意境。”三是“月亮创造了温馨绰约、淡泊朦胧的审美物象。”四是“月亮以其内涵丰富的原始意象,建立了一种不落言筌、不涉理路的审美象征形式。”上述四点几乎说尽了月亮意象的审美创造性属性,启人深思。第四节“月亮与中国文人的心象构成”以归纳月亮意象与文人审美心理的关联性,举头望月,寻找精神家园;冷月无声,寻求慰藉解脱;月影婆娑,企望归于山林。作者用心地梳理了月亮与中国艺术精神亲密的关系。《黄昏与中国文学的日暮情思》选取月出之前的黄昏时分,销魂的那一刻融入文本则会带来“有意味的形式”。作者摄取“瞑色起愁”以见黄昏意象的时间意义。这里有死亡迫近的忧惧、苍茫的历史意味、虚无的生命体验,“古老的黄昏里记录着我们民族情感和心灵的历史。”作者摄取“夕阳如画”以见黄昏意象的空间意义。审美意义分为三层:黄昏美学的形式层,黄昏美学的意味层,黄昏美学的意境层。从温馨愉悦的审美感受到静谧温馨的生命体验,再到以青山晚照、古道夕阳、落日余晖构成的群体意象,呈现出“那一刻”审美体验的意趣所在。作者摄取“落日催归”以见日暮人归的正题和反题。不错,黄昏的景象洋溢着回归的意趣,田园诗里的常见意象,读读王维、孟浩然的诗作便可领悟。女性的黄昏闺怨、游子的斜阳羁旅、友朋间日暮送别,构成了失意的主题。作者将失意看作反题,其实这是另一种意趣,日暮时分永驻的风景。作者摄取“寅饯纳日”以见黄昏意象的理论思考。看似摄取的四个镜头仅仅是“那一刻”,却带来了审美上的立体化效果,涵括了日暮情思的丰富内涵。
与太阳、月亮不同,森林根于大地,是人类实实在在的生存家园。《森林的象征及其文学的意蕴》从树木崇拜与宗教仪式的关系讲起。上古时期,森林是人类的原始栖居地,而后过渡到走向文明的木器时代,直至成为生命郁郁葱葱的象征。第二节“森林的祭祀与桑园的歌唱”是个吸引人的题目,作者认为:“桑园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特殊地位,一方面缘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活动中春天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生产方式,而另一方面则应看到在森林崇拜和神话传说中桑树也具有特殊意味。”[8]殷商时期的桑林祭祀、楚辞时代的扶桑书写,渐渐演变到新的主题,如桑园与文学的爱情主题、桑园与桑女文学主题、桑园与田园文学主题,从中能够聆听到农业文明时代古老民族的回声。森林与士大夫的林泉之致还是有关联的,只是不再是原始的森林意象,而是进入刻意营构的审美空间。一方面草木零落而悲秋,落叶纷飞叹飘零;另一方面苍翠欲滴见悦心,草木茂盛见隐趣,中国文人的审美心境落入花木丛中不可收拾。那么,森林意境的家园启示是什么?是物我浑融的温馨境界,是苍茫古朴的时间感受,是生机盎然与宁静悠远的审美意象,是一个民族审美心理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
轻风细雨,狂风暴雨,细雨行吟,骤雨洗心,从天空飘落的不只是凉凉的感觉,还有某种情景下的人生体验。那么,淅淅沥沥的雨是怎样打湿了中国诗坛?《雨:一个古典意象的原型分析》似乎为我们带来了答案。第一节“雨的祭祀及诗与雨之关系”从原始宗教祈雨中分析情感模式,原始祈雨是宗教活动与艺术活动的结合,而雨师是最早的一批原始歌手,祈雨辞是古老的歌谣。上述分析是依据文本展开的。第二节认为“诗人雨中吟唱存在着喜雨、苦雨、爱恋的三种情感模式”,有顺序地分析了祈雨原型与喜雨模式、洪水原型与苦雨情感、云雨原型与爱恋模式,每种模式均在文本细读中得出论断。第三节先是对准了凝愁的雨,点点滴滴、冷雨成为关键词;接着清凉的雨,洗尽人间利欲;而后是禅意的雨,充溢顿悟的哲思。第四节摄取“细雨微吟”探求“雨”意象中审美境界的构成。细雨中有迷离婉约的审美形态;有画意声情,创造出变幻的审美情境。总之,雨的意象组合形成一个内涵丰富的审美空间,进而促进现代诗的创作,体现了原始意象的现代价值。
三、文化意象与文化原型
所谓“文化意象”是指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创造的工具,因介入诗而具有特定的象征意味。日月星辰、风风雨雨,这些自然物象被人类赋予象征意义,而人类居于生存空间所创造的“门”“钟”“船”等文明物象同样具有象征意义。
我们所说的象征意义首先是建立在物质空间的基础上的,物质空间延伸出象征空间。人类找到一片空地,当用物质材料盖上房子,所谓的空旷便不存在了。房子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有门有窗,打开门窗才能走进外面的世界。封闭的和敞开的,构成了空间上的两个形容词,两个至关重要的形容词。《门:一个语词的诗学批评》考察的是“门”基于实用价值上衍生的诗学意义,藉以分析古代诗人的审美心理。第一节侧重厘清词语的意义,从本义、引申义到象征义,“门”从家园到具有社会文化意义,朱门、柴门是物质层面的,也会发生意义的升华,高门、寒门、门第、门阀却是文化社会学层面的。而后兼具艺术层面的象征意义,物意象成为诗人生命体验的化身。第二节干脆就定格在象征意蕴的探讨上,门的第一个象征意义是象征家园与世界,从特拉克尔到陶渊明,作者认为:“门的象征层次里把人类生存空间划分成家园与世界两个部分,人们漂泊于世界之中却无时无刻不向往家园。”[9]门的第二个象征意义是开启与关闭,寻常意义上的开门关门具有敞开与拒绝的含义。门的第三个象征意义是有门与无门,门指向路径,只有开门才会有人的流动。等待被邀请成为一种存在的常态,作者摄取三个镜头:一个是倚门而望,那是等待的呼唤;一个是长门怨,那是爱情的呼唤;一个是空门,那是解脱的呼唤。唐诗文本成为有效的例证。第三节“闭门:一个特殊的诗学意象符号”则追究“闭门”的意义所在。作者沉浸于唐人诗句中,第一义乃在隔绝,即逃避世俗与人群;第二义则在追求诗意的闲适;第三义则是敞开的精神世界。闭门可独居,闭门可孤芳自赏,闭门可拥有自由的精神空间。第四节对“门”展开审美分析,先是将“门”与古朴素淡的审美形式联系起来,以唐诗中的“柴门”相印证;再将“门”的时空意象组合与中国感伤美学传统联系起来,唐诗有黄昏的门,有秋天的门,有风雪中的门,这些组合被弗莱称为衰败的意象,正是中国古典感伤美学传统的表现形式;门与清净和宁静的审美感受息息相关,从空间到心灵,一个语词具有多元的文化内涵。
门是行走者渴望找到的出口和入口,门又往往将视觉文化与听觉联系在一起。“倚门”可见,“倚门”亦可听,见到的物象、听到的声音会别有意味。人类除了看见现实的世界,还需要倾听历史的声音。钟声响起,往往留下诗意的回响。《唐诗的钟声》无疑在《晚唐钟声》这部著作命名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何况“晚唐”仅仅是“唐”的一个部分。“唐诗中的钟声是耐人寻味的艺术意象,钟声悠悠,晨叩暮响,展示着唐代诗人丰富的心灵世界,表现出有唐一代独特的审美风韵”[10]。作者首先探寻唐诗钟声的历史意味,与日月星辰等自然物象不同,钟是文明物象之一。从青铜时代到乐舞时代,钟声经历了一个意象化进程,也是内涵历史化、艺术化进程。于是,古典时代的歌唱中便有了历史意味。作者从三个角度加以考察:钟负载着宗教祭祀功能,传达着人类对超自然世界的神秘理解;钟象征着政治的神圣威严,反映着古代礼乐之治的政治追求;钟声具有文化和人生品格的象征意义;钟声代表着时间的区分和苍茫的历史意义。根据上述四个方面,作者认为唐诗完成了钟声审美化创造过程,这个意象已经成为一个特定语词;完成了从儒家“钟鼓道志”向佛家空灵澄明的转变;声音效果上,从先秦两汉的浑融高古转向清凉淡远[11]。就此定格于唐诗世界,定格于对于梵意禅思的追寻。“在诗与佛的融和中,诗获得了丰富的思想蕴涵,钟声带给人的不是政治象征的高贵尊严,而是超尘脱俗的阵阵清凉”[12]。于是,钟声可以清心,可以传达出对于现实世界的否定进而追寻永恒的意蕴。倾听钟声就是倾听时间,钟声的时间意蕴缘于聆听。静夜闻钟、黄昏晚钟、晨钟晓钟呈现出各自的不同意蕴。“在晓、晨、晚、暮、夜几个特定的时刻,唐诗重视各行具有特殊的蕴涵”[13]。不仅有时间忧患,还有哲学的沉思。最后的部分回到唐诗钟声的修辞意义上来,以及透过修辞如何呈现艺术品格。主要探讨了空间形式上的高远清空特征,这是通过艺术组合实现的。作者举出夕阳晚钟、明月钟声、远山鸣钟,证实了“唐诗钟声的艺术品格是空间的、意境的,也具有时代的特征”[14]。从而能够涵养一个民族的文化和艺术精神。《烛光灯影里的中国诗》如同前面两篇一样,从“烛与灯”的艺术表现追溯原始意蕴,拈出“心灯”分析哲学与智慧的隐喻意义,《庄子》成为得出结论的元典个案。作者摄取灯烛的燃烧考察经典意象的构成,从情感形式到时空构成,再到审美形式,精神品格与审美意义结合起来了。最后是灯烛意象体现的人格精神,主要集中在照亮功能和悲剧意蕴。
当我们仰望星空,寻找月亮的象征意义,其实也在望月兴叹,我们只能站在地上按照圆缺盈亏生存下去,尽管飞升的愿望如此强烈。当我们徘徊水边,却可以找到凭依的木头做成船,有了船便可以之为媒介通向彼岸的目的地。人类的水上行进加速了文明的进程。船是一个流动意象,与漂泊连在一起。《船与诗:一种文明的思想与艺术考察》开篇就告诉我们:舟船的发明既是物质创造,也是文化创造和艺术创造。文章先是考察了舟船的发明及其文化意义,而后探寻《易经》文本中舟船的象征意义。后面的两节各执一端:一端是孤舟客船与古代诗人的精神世界,另一端是画船桨声里的审美意蕴。孤舟客船则关注舟船的诗化和意象化,分为四个方面:方舟意象的希望与获救意义,云帆行棹呈现出诗人的梦想和追求,孤舟客船与漂泊无依的悲凉心态,钓船归舟与逍遥自适的人格精神。画船桨声则关注审美交响效果,分为三个方面:春帆秋船与舟船意象的时间审美构成,夕阳月舟与舟船意象的空间审美境界,桨声画船与舟船意象的视听审美意蕴。无论是从思想上、象征上,还是从艺术上寻找舟船意象,船最终是属于诗的。如作者所说:“舟船的航行启迪了人类的智慧,更启迪了人类的无限诗情。”[15]唐诗里的舟楫客船是说不完的,作者沉浸在诗人寻找的世界里,以富有诗意的文字从文学上阐明了舟船的审美价值。乘舟远行所呈现出的审美意蕴是丰富的,客舟与家园的距离衍生出漂泊感,无论是“风正一帆悬”,还是“行舟绿水前”,都是远行者从“船”意象中确认“客”的身份,一旦身份确定了,“夜半钟声到客船”就将思与情融为一体去出发无限的遐思。
女娲炼石补天剩下一块石头,这块带有灵性的石头穿越远古走进人类的家园。石头,到底是自然意象还是文化意象呢?石头的构造可能是自然形成的,而形状却是经历打磨的过程的。何况从石头中还能提炼出金玉来。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对于曹雪芹来说是情爱的两个世界吧。《石头的言说:〈红楼梦〉象征世界的原型批评》读来极有吸引力,源自文化原型的呼唤,源自诗性叙事空间的构成。“石头是一种人格,它代表着与世俗抗争的人格风范和情操;石头是一种结构,它是曹雪芹构思《红楼梦》的结构线索;石头是一种传统,石头的精神规定性是从传统文化中获得的;石头是哀婉的,它代表着一代知识分子被弃的命运,反映着出世的清净的理想世界;石头是无言的,但它又是一种最深刻最彻底的哲学和艺术言说”[16]。归根结底,如作者所言,在曹雪芹的视野中,石头是《红楼梦》的中心意象,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第一节“石头的故事:《红楼梦》的四时结构”将大自然的四时结构与文学的四时结构联系在一起,分析叙事的发生、展开、高潮、结尾。故事之起乃在主人公贾宝玉衔玉而生,故事之承乃在摔玉而痴,故事之转乃在失玉而痴,故事之合乃在还玉而归。一块入世的石头化为宝玉,在对玉的追踪中演绎了一个富有神话色彩的人间悲剧。第二节“石与玉:《红楼梦》里的两个世界”则比较石头与玉的符号象征意义。《红楼梦》里有两个世界,一般来说分成大观园和以外的世界。大观园则是贾府里的伊甸园,允许纯情的存在,却也沾染了世俗风尘。在作者看来,自然的石头和打磨后的玉完全不同,原因有三:石头代表的是自然是原始是不假雕琢的本真,石头象征着傲岸孤介独立不群超凡脱俗的人格精神,石与玉是代表着不同人生体验的哲学语言。第三节“哀婉的石头:贾宝玉的双重角色”则将顽石精神与通灵宝玉并置,这块来自远古神话世界的石头与世俗斗争而又被世俗改造,贾宝玉的人生是充满矛盾的。第四节“石头的来历:顽石意象的文化和文献来源”则从文学文化角度切入主题,厘清了《红楼梦》与中国文化的相关性。《红楼梦》的石头意象“联系着复杂的敏感的中国古典哲学和艺术的神经,它汇聚了从女娲补天到三生石,从禹贡‘怪石似玉’到苏东坡‘尤物已随清梦断’的丰富历史内容,因此叩响了石头就如同叩响了历史和艺术的钟声,使我们听到了千百万个石头的歌声”[17]。第五节“石头的言说:石头的语言及修辞意义”则从审美维度上加以申说,认为石头高扬了尚奇的审美风范,石头美学是宁静的,具有伟大的艺术震撼力。一块石头包孕着整个世界,自然的石头与可以雕琢的玉放在一起,意象本身便指向隐喻的功能。这个隐喻又与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构成叙事进程的一条伏线。叙事的阶段性一方面融入文本的整体性之中,另一方面会从整体中凸显出来而成独立的叙事单元。从爱情到婚姻,从相聚到离别,从生存到死亡,人物形象的塑造均围绕着隐喻功能展开,叙事主题就在“石头的言说”中得到彰显。
一种文化与另外一种文化的融合往往要经历一个过程,融合过程中自然会逐渐形成新的审美样态。“随着一种文化与他者接触的频率增加和程度加深,以民族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世界观和自我意识有所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对传统的反思和对昔日身份认同形式的审视与强化”[18]。借助一种文化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内蕴的丰富性和民族性特征毫无疑问是可借鉴的有效手段。巡礼于中西文化的长河中,拈出原型,摄取兴象,再畅游中国文学的海洋里,寻找太阳和月亮,寻找大森林,寻找黄昏细雨,寻找门,寻找船,寻找烛光灯影的光亮,寻找石头的象征意义。其实,作者一直立足于中华文化的沃土,捕捉自远古而来的歌声,寻索人类的精神家园,发掘中华古典时代的文学传统,进而还原人类惊心动魄的审美历史。 历史是无声的,这些自然意象或者文化意象却一直都在。
时过境迁,有些文字自然会被忘记,有些文字则汇入学术史的长河之中,不仅是追溯过往的文化记忆图景,而且成为指向未来的学术灯塔。这部命名为《晚唐钟声》的著作既非“晚唐”,亦非“钟声”所能限制,而是对中国文学原型批评的全面考察,从中发掘出中国文学的审美价值。这是一次意象史意义上的美的巡礼,作者以所摄取的自然意象和文明意象建构了中华民族早期文化的精神家园,从而形成了研究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方法,具有拓展文学文化研究路径的典范意义。
[1][3][4][5][6][7][8][9][10][11][12][13][14][15][16][17]傅道彬《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第6页,第9页,第11页,第33页,第41页,第96页,第168页,第192页,第201-202页,第207页,第219页,第226页,第310页,第312页,第341页。
[2]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页。
[18]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会议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9页。
(作者单位: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