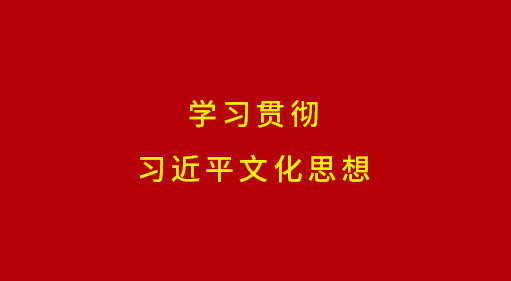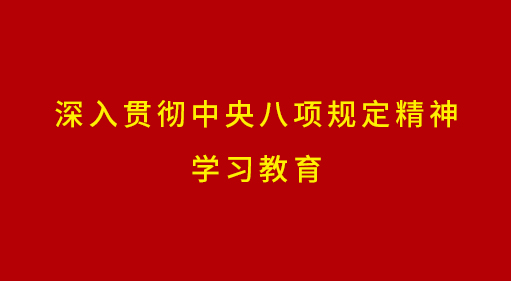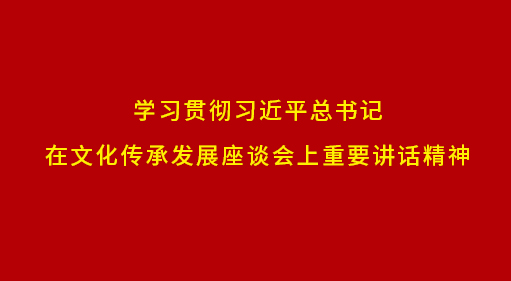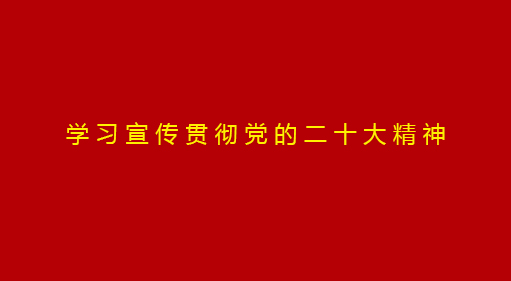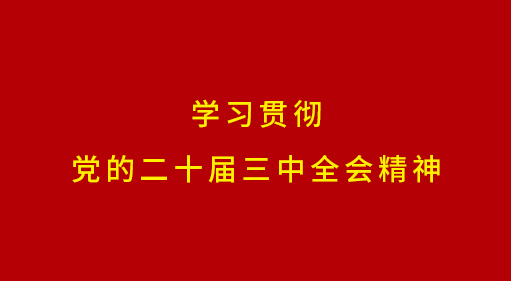电影《千钧一发》获奖拷问中国影视——如何再现先进人物艺术形象问题
时间:2009-07-22
2008年,在上海第十一届国际电影节上,反映黑龙江公安先进人物生活、绝大部分演职人员为黑龙江公安机关非专业工作者的电影《千钧一发》获得了五个奖项。尤其是获得了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演员奖两项大奖,成为了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大赢家,着实让中国电影在世界舞台上风光了一把。最近,在刚刚结束的第九届中国华语传媒大奖评选中,我又因为编剧《千钧一发》而获得了最佳编剧提名奖。一年来,不断有人问我影片为什么能够获奖,甚至有人是在尖锐地指出了影片的诸多毛病之后质问我,为什么能够获奖,言外包括了或多或少的潜台词: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和评委会的人有什么“特殊关系”?动没动用“潜规则”?有没有贿赂评委?等等。至此,我不得不做进一步的思考了。而思考的结果,就是我深深地感到,我们不能不考虑中国的影视创作、尤其是反映先进人物生活的影视创作该往何处去的问题了。
毋庸置疑,电影《千钧一发》是存在一些毛病,至少,她不能算是至善至美的。但是,她得到了评委会的一致认可,也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演员奖这两项大奖,7个评委是全票通过的,这也是事实。那么,在沉寂了许多年之后,中国的电影又因为《千钧一发》在国际影坛上大放光彩,这究竟为什么呢!对此,从表面上看,这不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按照一些资深的电影界人士的说法就比较简单了,他们说就是因为这部影片比较“真实”。我对此表示认同,但不敢苟同,因为,如此说未免有些过于片面了,更深刻的东西似乎没有说出来,也可能是他们认识到了更深刻的东西,但不愿说出来,那么,我就装一把内行,还是把它说出来吧!当然,首先,我得告诉大家,导演高群书率领的这支《千钧一发》“杂牌军”与评委会之间没有任何“特殊关系”!7个评委中,有2个是中国人,5个是外国人。5个外国评委我们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和人家建立起什么特殊关系,2个中国评委一个是王家卫,一个是陈冲,而在此之前,我们只认识陈冲,而且还是在银幕上,生活中根本就没有见过面。也不可能动用“潜规则”。因为,就我们这些“杂牌军”,人家也不可能看上我们。至于贿赂评委,也不可能,除了导演高群书外,我们根本就没有和评委接触的机会,按照公安侦查术语讲,叫“不具备作案时间,可以排除”。那么有“作案时间”的就是老高了,但老高又是个清高得了不得的人,他耻于演艺圈里的那些狗苟蝇营的事是出了名的,所以我想,他还不至于因为这次得奖而失身一把吧!那么既然如此,还是让我们从这部电影本身的艺术性来考虑吧!
我的感觉,这部电影能够获奖,至少给中国影视,尤其是以反映先进人物生活为表现题材的影视作品以这样几点启发:
首先是必须尊重生活,彻底从塑造人物的“高、大、全”和“假、大、空”传统模式里走出来。说到这儿,想起了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小说《野性的呼唤》开头的一句话:“因循的枷锁沉重难档”。看来,这“因循的枷锁”有时的确“沉重难档”,反映到影视创作上就是如此。因为,批判塑造先进人物的“高、大、全”已经不是今天的事情,而是打倒了“四人帮”、中国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来临时的事情了,但是,时至今日,在我们的一些影视创作上,仍然没有摆脱这个“因循的枷锁”。看看我们的有些反映先进人物的影视吧!差不多只要这个先进人物一出场,人们就会认出来:这是英雄人物。这几年,公安影视创作异军突起,但也没有摆脱这种模式,银幕上的那些公安局长、刑警队长,不是高大威武,就是深沉凝重,好像思想家,不逊救世主,然而,生活哪是这个样子啊!我接触的基层公安机关的局长、刑警队长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好骂人,有时甚至好打人,这是他们长期和犯罪分子接触时落下的“毛病”。试想,面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刑事犯罪分子,他能不骂娘吗?一个公安局长面对残暴的刑事犯罪分子,骂两句娘就有损公安机关形象了?根本就是“非也”!这一点,军事题材影视创作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公安影视创作,《亮剑》里的李云龙几乎不骂人不说话,但影响了李云龙这个人物的形象了吗?不但没有影响,还强化了他的性格。前不久和几个影视圈的朋友谈关于拍摄根据王江事迹改编的电影事宜,闲聊中,有人给我说了一个细节。他认为这个细节十分感人:有一次王江接受省委书记的接见,省委书记觉得王江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应该得到提拔,但王江说:不行啊!书记,不能再提拔我了,我已经是副科级干部了,在我们那儿方圆百里,就我一个副科级干部,连我们的所长还不是副科级呢!这是实事。但是,我听了说:实事肯定是实事,但如果你作为电影细节表现出去,观众肯定不会相信。观众不相信就没人看你的电影。生活中的真实不等于艺术上的真实。回头再说《千钧一发》,她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跳出了这种模式。首先是最初拟拍这部影片时的定位就力求跳出过去影视反映先进人物的模式。当初导演高群书第一次来黑龙江筹拍此片时,曾经就影片定位的问题和我一起试探性地征求过后来的本片监制、黑龙江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陈晓林的意见,陈晓林主任直截了当地说:“说真的,现在我们的一些公安题材影视片,我们好多公安机关内部的人都不愿意看,为什么呢?就是太‘正’了,离生活太远了,看起来不可信、不可爱、不可亲,甚至不可学。你要拍根据我们的英雄于尚清事迹改编的电影,我们大力支持,但你应该拍出一部让人感到、尤其是让我们公安机关内部的人看了感到老于这个人物可信、可爱、可亲,又可学的电影。”这番话听起来简单,但细分析起来便不是那么回事了,因为言外之意是说,你如果还是像过去那样,拍出一部“口号式”、“说教式”、公安机关内部的人都不愿意看的反映公安民警先进人物的电影,那么对不起,我们不支持。这番话,实际上成了我们后来拍摄电影《千钧一发》的总的基调,等于给“定了调子”。后来制作的全部过程基本都是按照这个调子来操作的。比方说在选择对于影片来说至关重要的于尚清的扮演者、男一号演员时,各级公安机关给高群书推荐了百十来个警察,有的是长相酷似于尚清的,有的是神似于尚清的,有的是具有很深的表演水平的,但老高一个都没有相中,原因就是,这些人太像警察了,而为了跳出过去反映先进人物影视的模式,老高从选演员开始就严格把关,坚决找一个“不像警察的”的警察来演警察。因为一般来说,警察都有一种特质,一出场人家就会认出你来。而我们就是要选一个放在普通人中,谁也看不出他是个警察的警察来演于尚清。这也符合生活原型特征,生活中的于尚清就是一个小人物,放在一百个人当中,谁也不会相信他能做出排除十枚定时炸弹的壮举来。
再就是要想拍出好的反映公安民警先进人物的影视剧,必须得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各行各业都在倡导,在影视制作上也不例外。那么具体说,到底需要“解放”什么“思想”?“更新”什么“观念”呢?我的理解,起码要注意摈弃以往的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理念”。当然这话仅限于制作反映先进人物的文艺作品。因为先进人物本身的事迹就已经高于生活了,就已经具备艺术形象所具有的东西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去人为地拔高,展现出来的艺术形象,肯定是脱离实际的,因而也是不可能让人们所接受的,也因而不可能让观众信服和喜爱。电影《千钧一发》之所以能够获得国际性大奖,我们恰恰是在这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比方,拍摄过程中,有人看了一些先期拍出来的毛片后,曾经建议高导和我:这样一部反映公安机关知名度比较高的先进人物的影片,是不是有意识地让主人公“老鱼”说几句有点“高度”的话,但我们经过反复研究,最后还是给予否决了。我们遵循的原则就是:“生活啥样就啥样”。“老鱼”最后一次排除炸弹被炸成重伤那场戏是全剧的最高潮,按照常规,这里边是断然要有英雄的一些“豪言壮语”的,但我们仍然按照生活的原样来写、来拍,结果这些“豪言壮语”成了“老鱼”在这时向领导“谈条件”了,他说:“局长,这次‘老鱼’弄不好就要灭火(牺牲)了,过去没有求过你们什么,现在我得说了。我妻子没工作,孩子当兵刚回来,工作也没有着落,如果我灭火了,你们得给考虑考虑这些问题呀!”试想,过去我们的一些反映先进人物的影视作品,有几个能这么表现英雄人物的最后时刻呢?
还有就是必须防止影视“贵族化”倾向,倡导小成本制作和非专业化的群众性参与,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影视制作中来。我没有做过调查,但我敢肯定,在近年来国际性电影评奖中获奖的影片中,电影《千钧一发》的制作成本是最低的。她总共才用了三百多万元,与那些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投资相比,这点钱简直就是九牛一毛。然而,就是这九牛一毛拍摄出来的电影得奖了,而且得了让人眼红的大奖。这起码给我们的影视制作者这样一个启示:不一定投资多就能拍出好的片子,也不一定投资多就能得到评委会的青睐,把大奖拱手送给你。作为一种事业,她想要发展进步,必须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大多数人的参与。有数量才能有质量。电影业也是一样,你动辄几千万,谁能拍得起?而且,这几千万都让谁拿走了,真正用到了制作上了吗?非也,绝大部分让那些参与拍摄的明星们拿走了。电影《千钧一发》没有用一个明星,也仅仅用了一个专业演员,其他全部是非专业化的警察“群众”演员。而如果我们把他们拒之门外,那么能有今天这个结果吗?如果大家对影视片昂贵的制作费用都望而却步,对身价百倍的影视明星都敬而远之,那么,我们影视制作业的发展繁荣可能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
综上,我感到,如果不改变上述三个观念,中国电影想走国门,走向世界,想融入世界文化的主流,与世界文化接轨,那将是一句空话。